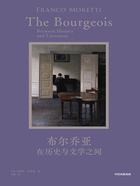
七、“布尔乔亚已无可挽回……”
1912年4月12日,所罗门·古根海姆(Solomon Guggenheim)的弟弟本杰明·古根海姆(Benjamin Guggenheim)正在“泰坦尼克”号游轮上,当船开始下沉,他是那些人中的一个:他们帮助妇女和儿童登上救生艇,同时要抵挡其他那些男性乘客的愤怒,有时甚至是暴行。当他的管家奉命司掌其中一艘救生艇时,古根海姆向他辞别,要他告诉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位女士因为本·古根海姆是一个懦夫而被弃置在船上。”仅此而已。[1]他的言辞可能难以引起共鸣,但这真的无关紧要;他做了正确的、做起来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当一个研究者为卡梅隆(Cameron)1997年公映的电影《泰坦尼克号》挖掘到这则轶事时,他立即把它带给编剧,想获取编剧的注意:多棒的场景。但他遭到了断然的拒绝:太不现实了。富人不可能为怯懦之类的抽象原则而死。事实上,电影中那个模糊的古根海姆式的人物,试图用枪来挤出通向救生艇的路。20
“布尔乔亚已无可挽回”,[2]1932年,托马斯·曼在论文《歌德——布尔乔亚时代的代表》中写道,而这两个泰坦尼克时刻——位于20世纪遥相对立的两端——同他的说法正相一致。布尔乔亚无可挽回,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无可挽回:相反,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如果,它同泥人似的,应该大部分都在毁灭当中)。已经消散的是布尔乔亚的正当感(the sense of bourgeois legitimacy):是这样一种观念,即统治阶级没有在统治,但它应该(deserves)去统治。正是这样一种信念,激发古根海姆在“泰坦尼克”号上说出那样的言词;用葛兰西讨论霸权(hegemony)概念的那些短文中的说法来说,此时处于生死关头的,是他所在阶级的“声望(及由此产生的信任)”。[3]放弃它,意味着失去统治的权利。
权力,由价值来证成。但是,恰恰当布尔乔亚的政治统治最后要提上议程的时候,[4]有三件重大而又新奇的事情,迅速而连续地出现,永远地改变了这一图景。首先到来的是政治的衰败。当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5]走到它艳俗的终点,就像那场它喜欢从中照见自身的轻歌剧,布尔乔亚什会同旧权贵把欧洲抛入战争的残杀之中;此后,它把自己的阶级利益荫庇在黑衫军与褐衫队(black and brown shirts)之后,[6]为更恶劣的大屠杀铺就了道路。当旧制度行将结束,新的人证明他们还没有能力像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那样去行动:1942年,当熊彼特带着冷酷的鄙视的笔调写道,“布尔乔亚阶级……需要一个主人”,[7]他不需要解释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21
第二次变换,性质上与第一次几乎完全相反,它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民主制度的广泛确立。佩里·安德森写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大众所达成的历史的合意(historical consent),其特性”是
大众的这样一种信仰:在现存的社会秩序中,他们握有最终的自我决定权……是大众的这样一种信念:在国家的治理中,所有公民都享有民主的平等——换句话说,他们不相信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8]
欧洲布尔乔亚什曾经把自身隐藏在一排排制服背后,现在则逃匿在一个政治神话——作为阶级它必须自我谦抑——背后;逃匿在一个伪装的行为背后,而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话语使伪装变得更为容易。于是,大功告成;当资本主义给西方大量劳工大众的生活带来了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福利,商品变成了新的合法化(legitimation)原则:合意(consensus)被建立在物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更不要说建立在原则基础上了。这就是今天的拂晓时刻:资本主义胜利了,布尔乔亚文化死了。22
本书遗漏了许多事情。有一些我已经在别处讨论过了,感到自己没有什么新的话要说:如巴尔扎克的“暴发户”(parvenus),狄更斯的中产阶级,曾在我的《世界之路》(The Way of the World)与《欧洲小说地图集》(Atlas of European Novel)中扮演重要角色。至于19世纪晚期的美国作家——诺里斯(Norris)、豪威尔斯(Howells)、德莱塞(Dreiser)——他们似乎没给这幅概括性的图画增添什么东西;再说,《布尔乔亚》是一部有所偏向的论文,没有百科全书式的野心。即便如此,有一个主题,我本来很想囊括进来,如果不是它威胁说自身可能要变成一本书的话:这就是维多利亚英国(Victorian Britain)与后1945年的美国之间的平行比较,它们凸显了这两种霸权性的资本主义文化的悖论——目前唯有这类文化存在——但却主要立足于反布尔乔亚的价值。[9]当然,我也在思考宗教情感在公共话语中的普遍存在;事实上,这样一种存在一直在扩张,并在急剧逆转它早期的世俗化趋势。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晚期的巨大技术进展来说,同样如此:工业“革命”与随后的电子“革命”并没有为理性主义的心性提供支持,相反,它产生了科学文盲与那种违抗信仰的宗教迷信——这些方面,现在比那时要糟糕得多。在这个方面,美国把维多利亚时代那一章的中心主题激进化了:韦伯式的祛魅(Entzauberung)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带的失败,社会关系的感伤的复魅(re-enchantment)对韦伯式祛魅的取代。维多利亚英国与后1945年的美国这两种情形都有一个关键的成分,那就是民族文化的剧烈婴儿化:从“家庭阅读”的虔敬观念——这开启了对维多利亚文学的任意删改,到糖浆式复制品:一家人,对着电视微笑——这推动着美国娱乐业走向安乐死的状态。[10]它们之间的平行线能够延伸向几乎每一个方向,从追求“实用”知识与大力强调教育政策的反智主义——它开始于对运动的沉溺——到“诚挚”(那时)与“有趣”(现在)等词语的普遍运用,它们几乎不加掩饰地鄙视知识上与情感上的严肃性。23
作为今日维多利亚主义的“美国生活方式”:一个具有诱惑力的观念,而我非常清楚我对于当代事态的无知,因此决定拒绝这一观念。这是一个正确——但困难的决定,因为它意味着承认《布尔乔亚》是一个纯粹历史性的研究,同当下没有任何真实的联系。在[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颠倒错乱与早年的伤痛》(Disorder and Early Sorrow)中,科内利乌斯博士(Dr Cornelius)暗想,历史学的教授们“之所以喜欢历史,不是因为它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仅仅是因为它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们的内心属于有条理、有章法的、历史的过去。……过去是不朽的;也就是说,它是死的”[11]。与科内利乌斯一样,我也是一个历史学教授;但我倾向于认为,章法分明的无生命之物,或许并不是我力所能逮的。在这一意义上,把《布尔乔亚》题献给佩里·安德森与保罗·弗洛雷斯·达凯斯(Paolo Flores d’Arcais)所表明的不仅是我对他们的友爱与敬重;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希望:有一天,我将从他们那里学会,将过去的知识用于当下的批判。这本书还没有达到这一希望。但下一本书或许可以。24
[1]John H.Davis,The Guggenheims,1848-1988:An American Epic,New York,1988, p.221.
[2][译注]中文译文见托马斯·曼著,朱雁冰译:《歌德与托尔斯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0页。
[3]Antonio Gramsci,Quaderni del carcere,Torino,1975,p.1519.
[4]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布尔乔亚什曾经是“历史上第一个取得了经济主导而不追求统治的阶级”,它是到“帝国主义时期(1886—1914)”才实现其“政治解放”的。见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1994(1948),p.123。
[5][译注]“美好年代”指的是欧洲社会史上从19世纪末到一战爆发的这段时期,此时的欧洲经济繁荣,社会和平,所以欧洲上流阶级称之为“美好年代”。
[6][译注]黑衫军:国家安全志愿民兵,意大利在一战后成立的法西斯准军事组织,因其成员着黑色制服而有此称。褐衫队:即冲锋队(Sturmabteilung),德国纳粹的武装组织,因其队员穿褐色制服而得此名。
[7]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 and Democracy,p.138.[译注]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第220页。
[8]“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I/100(November-December 1976), p.30.
[9]在通常的使用中,“霸权”这一术语涵盖着在历史层面和逻辑层面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和一个社会阶级对其他社会阶级的霸权;或简言之,国际的霸权和国内的霸权。英国和美国是到目前为止仅有的两个国际霸权的例子;当然还有许多国内霸权的例子:诸多布尔乔亚阶级以多种方式运用着它们对内的霸权。在本段以及在《雾》那一章中,我的论述涉及一些特定的价值,我把这些价值同英国和美国的国内霸权结合了起来。这些价值与那些培植了国际霸权的价值是怎样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但那就不是这里要讨论的对象了。
[10]显然,这两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讲故事的人——狄更斯与斯皮尔伯格(Spielberg)——都专攻既吸引儿童也吸引成人的故事。
[11]Thomas Mann,Stories of Three Decades,New York,1936,p.506.[译注]中文译文见钱鸿嘉、刘德中译:《托马斯·曼中短篇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3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