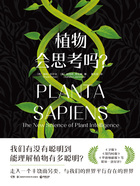
前言
多年来,我一直在试着理解一类与我们相差很大的生物的体验:我想要揭开植物智能的本质。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课题。虽然相关的科学研究还远未完成,但是我们迄今的发现已经向我们指出还要找寻什么了。这本书是我对过去二十年激情探索的总结,探索的对象是一个丰富而另类的世界,它与我们的世界平行存在着。
我的冒险始于2006年,那一年我读到了一本从神经元角度探讨植物生活的书,由弗兰蒂泽克·鲍卢什考(Franti ek Balu ka)、斯蒂法诺·曼库索(Stefano Mancuso)和迪特尔·福尔克曼(Dieter Volkmann)三位科学家编纂。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古怪:植物哪来什么神经元呢?我自己也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植物。但是第二年,我在斯洛伐克的上塔拉特山参加完植物神经生物学学会(Society of Plant Neurobiology)的一场会议之后,却不禁为这个想法深深着迷。接着我就踏上了一段漫长的旅程,去往世界各地,从英国伦敦、爱丁堡和美国纽约的植物园,到印度、中国、巴西、智利和澳大利亚,甚至还有毛里求斯的雨林。但是,我在物理上穿越的距离,远不能和我在精神上踏足的领域相比。
在这项研究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人类会不由自主地从个体经验中得出关于世界的宏大结论。这固然是我们成为智慧生物的原因之一,但也使我们的眼光格外狭窄。
即便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家,也不免会表现出目光短浅的倾向。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曾经在我们的思想史上种出累累硕果,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却真切地反映了他们的局限性。在古希腊人看来,希腊的权力中心德尔斐神庙也是世界的地理中心。他们将这座神庙称为“翁法洛斯”(Omphalos),即世界的肚脐。据说宙斯曾在世界两端放出两只一模一样的鹰,而德尔斐神庙就是它们的会合之处。神庙里的德尔斐神谕受到古代世界的一致推崇。朝圣者会连日步行来到帕纳塞斯山脚下的这处圣所,因为向德尔斐神谕求教就等于直接拉扯宇宙的脐带。
我本人也在2019年来到德尔斐,来参加一场思想者的盛会,与会者包括哲学家、科学家和创作者。我们的这次会议是为了探讨人类在世界上的地位。说不清是出于真诚还是反讽,我们将开会的地点选在了这个古典世界的肚脐,在这里思考人类自恋自大的习性,并设想该如何超越这种自大。古希腊并不是唯一患上“翁法洛斯综合征”的文明,即相信自己的社会政治中心也是宇宙的中心。这是从古至今延绵不绝的一种习性: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社会,我们都有一种认为世界围绕我们运转的倾向。这让我们惹出了许多麻烦,有生态的、政治的,也有心理的。如今,这群无畏的思想者在德尔斐齐聚一堂,为的是解开人的本质、人类与环境互动的本质。我们要找到新的思考方式,以适应一种不同的将来——那或许能使我们与其他生物的联合变得更加成熟和紧密。
那个周末,我们有幸探访了当地的考古现场。当我站在这座阿波罗神庙废墟前的大片空地,环顾四周的褐色碎石山坡时,我想到了据说曾经镌刻于其上的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这是一条简单的训示,却也是一个人一生的修行。它肯定不是一百个人开一场会就能解决的,即便那一百个人都是知识分子。我当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我们要换一种非常不同的思路,才能深入思考这些问题,从其他物种身上获益,进而以新的眼光探索自己的心灵。但当时的我还不明白,我的思路转换将会到达怎样的程度。
德尔斐的经历深深改变了我。它的风景本身已经反映出我们想要解答的问题:浓郁的历史气息与鲜活的现实相互交错,考古遗迹静卧在葱郁的森林和草地中。然而面对这样一片景致,我们却只看到些残垣断壁和过去留下的微弱痕迹。我们只隐约注意到了这里的生物正进行着活动,人类的造物则被它们当作活动的舞台。在这里,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要“认识你自己”,你的思想就必须远远超越自身,甚至超越自己的物种。一个人只有了解了他者,才能认识自身。我们必须去思考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生物的体验,无论它们是多么原始或多么复杂。它们与我们是如此不同,乃至它们的体验可能并不来自我们熟悉的动物式的思考机制,无需大脑、神经元或是突触。就这样,我思考起了植物的智能。
我们都深深地被禁锢于智力源于神经元、意识源于大脑的想法,很难想象还有其他类型的内心体验。这本书光是书名本身就可能引发一些人的嘲笑与惊愕。这也可以理解:它毕竟质疑了人类体验的根基。为了勾勒一幅不使用大脑思考的图景,本书将会触及神经科学、植物生理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前沿课题,并深入探讨身为一株植物可能是怎样的感受。我将会播下几粒科学证据的种子,并谨慎地观察它们会随着研究的进行长到哪里。
谨慎是必需的:无论你是对植物拥有智能的说法深表怀疑,还是对其他生命形式拥有超自然智慧的理论热切相信,都要谨慎地拓展思维。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或将彻底改变,但这种改变也必须有所节制,要随着证据的浮现步步为营。我既不想狭隘地无视科学正在揭示的惊人可能,也不想开创一种新的万物有灵教,鼓吹自然崇拜。这本书是写给每一个人的,你既可以认为植物可能有智能,也可以认为它们不可能有。无论持有何种成见,你都会在书中遭到挑战。所以不妨抛掉成见,打开心灵,踏上证据为我们铺设的道路——如果我们准许自己看到这条路的话。
前方的发现或许会吓到我们:理解这世上其他的生存方式,很可能会让我们明白人类的智能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独特。我们才刚开始承认人类以外的动物或许也有智能,再要接受植物可能也有,就需要彻底转变思路了。在某个空想的等级体系中失去自封的至高地位,或许会令人感到屈辱,但如果真能转变认知,就会获得奇妙的奖赏。关键是,套用荷兰灵长类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的一句问话:我们有没有聪明到能理解植物有多聪明?或许还可以追问一句:我们有没有这个勇气?
这项研究始于我们自己的头脑。查尔斯·达尔文在发展他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时,使用了一件非常强大的工具,那不是科学仪器或者生物样本,而是他自己的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每一天,早晚各一次,他都会沿着肯特郡唐恩村(Downe)自家土地边缘的一条砂石小路行走,小路名叫“沙土道”(Sand Walk)。他将这条路线称为自己的“思想小道”(thinking path)。无论下雨、天晴还是雨夹雪,达尔文总会在沿途植物和动物的陪伴之下,思索他的阅读、通信和实验。和许多思想家一样,他喜欢用身体的运动来推进思维,并帮助想法生长。
在为写作本书开展的旅行中,我原本希望最后一程能前往达尔文的故居,像他一样亲身体验一回那条砂石小道在我的脚下嘎吱作响的感觉。我已经想好了在那片女贞篱笆和乔木的环绕中写下这篇前言,当年它们也曾弯下腰来,倾听达尔文那严谨而博大的思想。但悲哀的是,新冠疫情的阻隔使我不能亲自去那里朝圣。作为替代,我只能在内心重走了一遍我自己的“思想小道”,那是我在过去二十年间为理解植物智能走过的一条心路。那也是一条漫长而丰饶的路线,它点燃了我的畅想,开拓了我的思维。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同上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