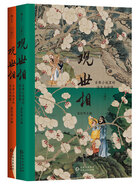
一
《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度
就“魏晋风度”而言,其肇端固然在一千六七百年以前的魏晋之际,但其真正凝结成为一大概念,则历时尚不足百年。
1927年7月,在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举办的“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时年四十六岁的鲁迅于23日、26日分两次做了现在看来十分重要的演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3]。在这篇将近一万字的演讲稿中,鲁迅谈到了三个方面:一是魏晋文章及其特点,概括下来就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二是以“正始名士”何晏为祖师的服药之风;三是以“竹林名士”为代表的饮酒之风。除了题目,正文中并未对“魏晋风度”做具体阐释,但鲁迅的意思应当是:魏晋文章及名士们煽起的服药与饮酒两大风气,便是“魏晋风度”最重要的表现及展示。此后,“魏晋风度”便成为一大文化关键词,以之为题做文章者代有其人,层出不穷。
1940年,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问世。在这篇屡被称引的论文中,宗先生开篇就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4]宗先生以反差的形式揭橥了魏晋时代的“艺术精神”,堪称孤明先发,振聋发聩。此外,还有两个论断深具卓识:一是“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二是“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这两句话本身也可说是中国美学史上的重大“发现”。
1944年,哲学家冯友兰发表《论风流》一文,将“魏晋风度”张大为“魏晋风流”。在谈及名士之人格美时,冯氏称:“是名士,必风流。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假名士只求常得无事,只能痛饮酒,熟读《离骚》。他的风流,也只是假风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风流若分析其构成的条件,不是若此简单。” [5]并进而提出,真名士必备之四个精神条件:曰玄心、曰洞见、曰妙赏、曰深情。进一步从人格美的角度深化了“魏晋风度”的精神内涵。
1948年,王瑶完成《中古文学史论》一书,在自序中,作者称该书第二部分《中古文人生活》“主要是承继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加以研究阐发的”。书中的《文人与药》《文人与酒》等篇什,后来成为研究“魏晋风度”的必读文献。
1981年,李泽厚《美的历程》出版,书中第五章题为“魏晋风度”,把这一议题的探讨和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在“人的主题”一节中,李泽厚提出了“人的觉醒”这一命题,认为正是“人的觉醒”才使“人的主题”提上日程,从而形成了汉魏六朝这几百年的人性大解放和艺术大繁荣。这就又把“魏晋风度”的内涵在美学和哲学向度上推进了一层,使铃木虎雄首倡、鲁迅复加点染的“文学的自觉”说有了一个更可靠的理论前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纷纷就“魏晋风度”著书立说,为丰富这一研究做出了贡献。我也曾以风俗为切入角度,将“魏晋风度”分疏为以下十二个面向:清议之风、品鉴之风、容止之风、清谈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隐逸之风、艺术之风、嘲戏之风、雅量之风、豪奢之风。除服药之风与豪奢之风外,其他十种风气均有正面阐释之价值。
所谓“魏晋风度”,是指汉末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时代精神和人格理想,具体就是指受道家学说和玄学清谈思潮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追求自然(与名教相对
)、自我(与外物相对
)、自由(与约束相对
)的时代风气,以及由此在上层贵族阶层中形成的,一种超越性的人生价值观和审美性的人格气度。此即我所谓的魏晋风度的“三自追求”。
进一步分析,每一种追求都有三个路径。如“求自然”可以从“容止顺自然”“思想尚自然”“居止近自然”三个方面来把握,“求自我”可以从“方外求我”“酒中求我”“情中求我”三个方面去认知,而“求自由”也可概括为“从隐逸中求自由”“从艺术中求自由”和“从死亡中求自由”三个层面。
总之,对“魏晋风度”的探讨与诠释,实际上隐含着近代以来“人性解放”与“人格独立”等一系列大问题、大考问,其中就包括人对于现实政治的超越以及个体人格独立的问题。鲁迅做完演讲后,在给友人的信中称:“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同样,研究“魏晋风度”,亦当存有反躬自问,重建知识分子风骨与精神之关怀。
“看似史而超越史,不是诗而胜似诗,并非哲学而富含哲学气质”,这就是《世说新语》带给人的充满哲思和诗性的审美愉悦。书中展现的“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至今仍令人心向神往。限于篇幅,下文我们且就清谈和隐逸两种风气做一个简单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