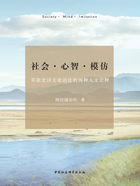
第二节 从形式到内容:作为文化语法的类型学
草原史诗的类型学(《〈江格尔〉论》和《源流》),把整个蒙古史诗的类型、发展和演化轨迹构设于社会历史和人文原型等综合基础和宏观复原模型,包括三组问题:发生学的前提或目的论、类型学的还原论或原型论、类型的发展论。因而,这种发生论、还原论和发展论,不仅是整个蒙古史诗类型学方法论的问题基础,同时也是类型学批评的出发点或归宿点。基于以上思路,史诗类型学的语法构建由以下三方面组成:以时空范畴的溯源方法为中心的发生论模式(产生年代和原发祥地),以社会文化的历史原型为基准的还原论模式(艺术本源的文化维度和社会历史的事件维度),以类型发展的分类学和分析方法为主线的发展论模式(形象和情节结构的类型及发展)。其中,社会历史主义和本土化的类型分析法的结合研究是以上三种考证模式的核心联结,也是类型学语法构建的实证根基。
史诗类型学的发生论。该论域从时空的范畴考察艺术化的历史源头,比较客观地回答了整个蒙古史诗的历时和空间范畴的复原问题;其维度包括产生年代和原发祥地两个支点,而且两者均属于目的论的前提范畴。其一,史诗类型学的历时发生论,在以俄苏和德国为首的西方学者的历史主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考证了整个蒙古史诗发生的多维历时表这一论题。即,以社会历史的反映论为主要依据,认为蒙古史诗文类的古老基础均产生于原始的氏族社会时期,并且史诗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诸如单篇型、串联复合型和并列复合型等三大史诗类型就分别代表了在这些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各种史诗文类的历史特征和演化情形。具体来说,早期巴尔虎史诗反映了原始社会的部落战争,而《江格尔》则记述了兴起于15—17世纪的卫拉特部落的社会文化与历史情形等。事实上,历时发生论不仅借鉴了弗拉基米尔佐夫(Б.Я.ΒладиΜирцов)、波佩(N.Poppe)、科津(Kozin)、桑杰(热)耶夫(Санжеев)和帕兀哈(Poucha)等有关《江格尔》产生年代问题的一些看法,还对把《江格尔》的产生年代追溯到15世纪以前的观点、将《江格尔》视作单一时间维度的历史产物的看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些有争议的观点包括:弗拉基米尔佐夫的“贵族起源说”、桑杰耶夫有关史诗类型的区域分布确定及层梯发展论、波佩关于喀尔喀史诗的社会历史原型论、米哈伊洛夫(Михайлов)有关“蒙古史诗产生于公元8—9 世纪至12—13 世纪”的看法,等等。其二,空间范畴论的地理学问题,与弗拉基米尔佐夫、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普罗普、梅列金斯基(E.M.Мелетинский)和涅克留多夫(S.J.Nekljudov)等所提出的“史诗共同体”这一观点有着密切的联系。突厥—蒙古史诗所反映的各部族社会历史的相似性正说明了以民族迁徙的社会背景为基础的起源上的古老共性:南西伯利亚的森林地区和中央亚细亚的北部地区是突厥—蒙古史诗的中心地带之一,而萨彦—阿尔泰地区则是突厥史诗的发源地。因此,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史诗共同体”之观点,从多方面综合地影响了类型学传播论之成形,并成为其方法论意义上的历时性条件或前提。即,传播论批评在以往空间范畴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挖掘,并推断出了蒙古—突厥史诗的核心地带和原发祥地:贝加尔河一带和与此毗邻的中亚北部、贝加尔河地带森林区。除了空间范畴的传播论之外,历史类型的探索模式也关涉类型学地理分布这一空间论范畴,指在历史上没有发生任何接触和交往的相似现象的类型学问题。
史诗类型学的还原论。该视域以艺术本源和社会历史的现实基础为准线,力求解答整个蒙古史诗所蕴含着的社会文化的历史源头问题。其基点包括两个核心内容,即艺术本源的文化维度和社会历史的事件维度,两者均属于类型方法论的原型分析学范畴。史诗类型学提出,早期蒙古史诗的主题来源于勇士(或英雄)的婚姻和勇士与蟒古斯的斗争,这些均产生于史前史或国家出现之前的历史时期;而《江格尔》作为国家出现之后的史诗文类之典范,源自早期的孤儿传说、历史化传说和其他不同的历时因素等综合基础。就从本源的文化维度和原型的时间维度来看,早期蒙古史诗反映了氏族社会的现实情境和生活画卷;而以《江格尔》中的社会状况、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社会军事的政治制度、社会各阶层的结构、人们的思想愿望以及经济文化状况等来鉴别,它与明代蒙古族封建割据时期西蒙古卫拉特地区社会现实相符合,反映了封建割据时期卫拉特地区的社会斗争和历史画卷。可以说,作为民间文艺作品,草原史诗并不是对那些历史过程的翻版或“忠实记录”,而是把部族社会的历史提升为典型事件,同时又大大加强了英雄史诗的社会学意义。很显然,类型批评的还原论虽然基本赞同了桑杰耶夫、米哈伊洛夫和涅克留多夫等有关史诗来源于早期宗教、艺术和具有多元结构的观点,但也提出了一些拓宽性和修正性的批评和意见。依照史诗类型学的田野工作观,展演事件的结构既是诸如情境化因素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又是介乎于文本和社会的关键性基架。
史诗类型学的发展论。该论域以人物和情节结构的分类学与发展为基本准线,阐释了整个蒙古史诗的历史结构与叙事发展论的关系问题。立论的维度包括形象和情节类型的分类学与发展论两个内容,两者均属于类型方法论的基础分析学范畴。其一,类型形象论偏重于人物功能的观察,不同于以往的和同一时代的学者们所提倡以主人公为中心的形象学方法,其强调的基准是以副手勇士为中心的形象学模式,认为有时副手勇士所起的作用比起主人公还要大一些。以《江格尔》为例,洪古尔作为人物形象群中的成功典范,是人民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创作方法来塑造出的艺术形象,在这类英雄人物身上汇集了人民群众的美好向往和思想愿望。因此,《江格尔》中的人物形象是以共性的传统为基础,以个性的发展为特征的类型体系;同一个人物类型上存在着的矛盾反映了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对立统一这一面。在此,类型形象学批评还抨击了根据史诗文类的表象因素而对社会结构和历史特征进行简单化推论的做法。史诗类型学方法认为,表象分析论的依据无疑来自与角色有关的宫殿、财物和武器的描绘、称谓关系、阶级结构等。因为,根据表象因素而对人物形象的阶级成分进行定论也是徒劳的,这种做法忽视了表象因素背后的历史演化及年代维度。从称谓的类型分析看,难以只凭借可汗、巴图尔和莫尔根等词语的现代(表层)含义而对其进行社会结构和文化层面的纵深观察。此外,形象特征与情节结构的对应关系也是形象论批评的重要依据,这种联结界定了形象论的社会原型和历史基础。即,过去把所有的可汗和勇士都归结成为酋长、首领或奴隶主的做法也不妥当,因为这种直观认识“没有什么根据”可言。情节结构的类型批评认为,决定史诗命运的是与社会历史息息相关的事件维度和现实因素,而不是来自泛文化论叙事维度的外在缘由。无论早期神话或传说的艺术要素,还是后期加入进来的佛教或其他文化的要素,这些必定都是次要的方面,而以婚姻和战争为基础的核心内容才是最主要的方面。史诗类型学还指出,桑杰耶夫和涅克留多夫等曾提出过以史诗的古老内容和神话成分为发展论基础的观点,但这也并不符合蒙古史诗的自身发展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