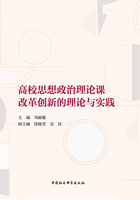
第7章 讲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第一课
左鹏[11]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式发展。正值人生“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在大中小学不同阶段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地接受着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既有差异性又有统一性的思政课教育教学。对于刚刚进入大学的新生来说,第一次拿到大学思政课教材、走进大学思政课课堂,普遍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大学生是从中学生而来的,中学生对于思政课的感觉,必然会被带到大学来,先入为主地影响着他们对于大学思政课的思想认知和学习态度。
那么,中学生对于思政课一般是种什么感觉?由于各种因素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中学都是把高考升学率、名校升学率作为追求目标,应试教育的倾向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思政课学习,主要是为上一所好的大学而掌握更多的知识,考出更高的成绩;教师的思政课教学,主要是把更多的知识填塞给学生,以提升学生的应试能力和技巧,至于对学生思想的教育和引导,暂时只能蛰居次要位置了。结果,划重点、背教材、不停地做题,就成了不少中学思政课教学的常态,学生对于思政课的印象差不多就剩下“靠着背诵拿高分”了,这也成了不少中学生在文理分科时选择理科的助推因素之一。
进入大学后,看到似曾相识的课程、教材,不少新生(特别是理科生)感到十分意外,怎么上了大学还要上思政课?这时,他们在中学阶段业已形成的对于思政课的刻板印象被激活了,不少人实际上是抱着很大的成见走进大学思政第一课的。这就使得大学思政课多了一个不同于其他课程的地方,学生在真正接触之前就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负面评价、消极心态。这不是大学思政课本身使然,而是中学阶段发生的问题延伸到大学的必然结果。
所以,讲好大学思政第一课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讲好这一课,可以澄清大学新生的思想困惑,改变他们对于思政课的刻板印象,为今后学好大学思政课确立良好的思想认知和学习态度;讲不好这一课,在一些大学新生眼中,大学思政课就是中学思政课的继续,中学期间形成的思想认知和学习态度就会很自然地延伸下来,影响着后续整个大学思政课的学习。
针对大学新生的思想实际,大学思政第一课不应只是大学开设的第一门思政课(多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导论,而应是大学整个思政课甚或整个大中小学思政课的一个总的导论。在这个导论中,要告诉学生,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而思政课是落实这一任务的关键课程。学校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是为了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精湛的专业技能,成为某方面的有用之才;对学生进行包括思政课教学在内的德育、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让学生确立正确的成才目标、人生方向。如果说专业课教学解决的是“用”的问题,思政课教学解决的则是“为谁用”“怎么用”的问题。
古今中外,每个国家的教育莫不如此。西方一些国家的学校中未必有显性的思政课教学、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但绝对有这方面的工作,而且还很有一套。它们往往是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政治养成教育、共同价值观教育等不同的名目下,进行了大量实质性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为名称所囿,就应该承认,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在每个国家都有,并不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更不是只有中国才有。打开了这样的国际视野,就可以帮助学生走出“西方思想自由,没有思政课”的认识误区,进而更自然地接受中国学校的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
鉴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再正常不过了。如果我们培养的只是旁观者,甚至是“不肖子孙”“精日分子”“吃里扒外”“吃饭砸锅”的人,那我们办教育干什么?引导学生有了这样的思想认识,学生就不至于把思政课看作不得已而学之的让人漠视甚至反感的课程了。只有让学生看到思政课对于自己未来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意义所在,才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
另外,还要使学生明白,大学期间学习思政课,尽管通常还要以考试来评价学习效果,但考试不是学习的主要目的,学习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确立并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告诉学生,大学思政课不同于中学思政课,不再以知识点的识记为主要考核方式,而是试行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把学生从习以为常的考试压力中解放出来,使他们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思想养成和素质提升而学习。
有了这么一堂大学思政第一课,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不少大学新生在中学阶段业已形成并固化下来的对于思政课的刻板印象,使他们由思想上重视到心理上接受,进而自觉地学好大学思政课,为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铺设好过渡的桥梁,搭建起跃进的台阶。
(本文原载于《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