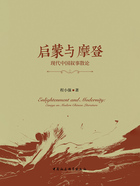
绪论
在阅读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我常常会面对一些一时半会儿并不能解决的问题。即以鲁迅而言,考以古者圣贤的选择,他们或处庙堂之高身怀治国安民抱负,或处江湖之远而立意福泽苍生。以鲁迅所受教育及日后职业选择而言,他大约认可这一传统中国知识人的选择。科举式微,鲁迅远赴东洋学习医术,若按这条路走下去,顺乎一般中国人的生存理想或成就一代名医。鲁迅赴日,面对的是一个强势崛起、对中华虎视眈眈的国家,但赴日生活数年间又不乏温暖的人事及生命细节,同时代留日群体的日本体验并不像后来所放大与想象的那般痛苦。那些留日期间温暖的人事仍培植与强化着鲁迅自少年时代以来在家庭败落过程中滋养的生命韧性。如此矛盾的环境叠合少年以来艰窘的生命体验,进而引发选择过程中的纠结自在情理之中。这必然促使鲁迅做出新的人生调整。数代学者已关注到日本体验对鲁迅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然而,所谓至今仍无法考证的“幻灯片事件”多少有修辞的成分,将一个人做出的关乎人生的重大选择仅仅建立在一次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件多少还是有点牵强。愚弱的国民并不是在日俄战争中才有的,鲁迅的写作及中国文学内外的记载都在显示愚弱已成为国民常态之一种,鲁迅后来回忆并强调“幻灯片事件”的巨大影响多少有些新历史主义所言叙事的味道。在日本,鲁迅显然经历了比较漫长的思考,并在1906年做出弃医从文的选择。多年来,学术界和一般知识普及几乎在无限扩大鲁迅弃医从文的意义。其实,按照鲁迅的新旧教育经历、成长体验与敏锐早慧之心思,即使从医,大约未必会妨碍一位伟大思想家的诞生,况且医学的救死扶伤职责与文学的启蒙疗救视野多有相通之处,更何况突破专业局限跨界从事文学创作本来就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常事。实则,由医而文并不全然意味着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全新鲁迅的诞生,我们必须重视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后岁月里的人生规划及实践,即他仍然上居庙堂为国事而劳心勠力。此番由文而仕的生活—职业选择其实为世人所熟知,但相应的无视或是教条式理解也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其实,无论鲁迅的思想意识与文学理想超前于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多少年,然而他毕竟也只是时代烟尘中的一粒而已,后来获得的思想与启蒙巨子身份与他作为一个辛亥革命以来的普通中国人的职业选择并不冲突。哪怕一个小小佥事并非所有收入来源,但鲁迅能在那么多年的日日点卯中坚持下来,由此可见这份差事对他而言仍然是重要的,即如其后来失去这份差事时的心情并不轻松无谓。
如果十余年佥事职业仅仅是个差事,那倒也罢了。若再细究之,十余年的中国高等公务部门干事的生活确实影响到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回到晚清民初的思想文化场,晚清以来的文化传播、文学译介、西学东渐等进行数十年,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渐次兴起。后来者看到的大都是西学影响,进而从晚清时期的“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话语中找寻近似的资源已是固化思维。这样的探寻路径是有其道理的,也早已成为学术共识。但若再联想一个常识,即一代五四启蒙先驱者大都幼承庭训,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青年以来忧愤于民族国家的积贫积弱,他们身上担负的中国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与启蒙时代中国的距离大约仅一步之遥。再试想,一个什么样的事业和一个什么样的岗位最符合他们的身份与理想?毫无疑问便是与官方、政府的合作。相比起进入民国大学当著名教授,入值官署是将个人融入时代大潮的最优途径。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历史叙事中的北洋政府如此黑暗反动,而那时的不少文人却大都有心入值官署。看起来矛盾的事情,实为兼善之选择。既然入值官署,那在其位谋其事的具体表征最应该是在一个不同于封建帝制时代的现代政府中,竭尽所能地治理国家,让国家通过有效的治理走向现代、富强、文明、科学。有了这样的出发点和使命,我们便看到了鲁迅及其文学创作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治理现状及治理能力的不满。这是启蒙文学的视野,也是中国传统知识人再平常不过的选择。
概言之,鲁迅在其小说及杂文中对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层面的中国治理现状极其不满,指出此类治理逆历史而动,反人性、反科学、反伦理、反道德及违背现代法理,乃至对传统中国“吃人”的社会本质无法做出有效应对。这些社会治理所涉问题包括历史伦理、乡村社会结构、弱者命运、青年男女解放、国民性、无效抗争、公序良俗、心理结构、权力结构、日常生活、农村破产、乡村流氓的改造及知识分子人格等。鲁迅的全部创作事实上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否定了辛亥革命以来的旧的治理模式和社会结构。本著所论启蒙诸文关乎宗法制时代的乡村治理危机、青年男女解放问题、革命时代的乡村一体化危机、个体的自我救赎问题,至于启蒙主义在革命退潮后(“后革命时代”)的社会历史—人心人性结构中仍有的强烈的现实性,成为鉴照每一个时代的中国治理不足的一面巨幅镜子,尤其是各个时代的启蒙者对中国农民生存问题的关注尤见出一个时代矛盾的尖锐与知识分子的良知。
对于启蒙主义,仍有一些问题需要交代。我从中国治理危机角度来思考鲁迅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关系,与启蒙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文学史、思想史并不冲突。启蒙是晚清民初以来国门开放后西学东渐、文化传播、民族国家走向现代之际的历史选择与必由之路,也是少年中国成长过程中的重大收获,鲁迅的文学与人生由此选择了在启蒙话语下探究中国的方式。只是在具体的探究过程中,现实的鲜活性肯定不是一个主义、话语所能涵盖的,鲁迅的思考即远超启蒙这一概括性的时代主潮。在中国治理视野及现实主义文学评价的时代性层面,鲁迅获得了与同代人的比较优势。随着革命时代的基本终结,鲁迅文学评价标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鲁迅代替革命鲁迅的评价标准确立,鲁迅文学的超越性论调获得深度阐发并影响了数十年的鲁迅研究、阅读与教学。其实,若从鲁迅经典地位的确立过程来看,无疑是辛亥革命以来的时代及相应的时代性文学评价标准确立了鲁迅的文学地位和意义,20世纪20年代末,太阳社攻击鲁迅等一代五四作家的过时论也是基于时代环境变化而发出的,偏颇与意气之争即来自鲁迅与革命主潮不太贴合。就此而言,鲁迅评价中时代性应是第一位的,而后来的超越性标准具备衍生特质,是鲁迅对辛亥革命及五四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深刻发现在各个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释而已,实在不应过于夸大与迷信任何作家的任何超越性的意义。任何一个时代的问题总是新旧杂陈,新问题还得由具体时代亲历者去发现、总结、思考与解决,所谓跨代超越性地解决了某些问题或者超前思考了某些问题等相应评价话语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工作不可能经由夸饰鲁迅的超越性文字—思想意义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事实上这一做法也是完全不靠谱和不负责任的。由此引出鲁迅文学的意义问题。他对自辛亥革命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观察深广度及思考敏锐度是其同代人无法企及的。这奠定了其文学(史)地位,这也再次强化了鲁迅文学的时代性意义。若按超越性论调将鲁迅写作的创作初衷及意义归置于百年以后的目下,那是谁都无法接受的。
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中国,启蒙成为一种思想方式。启蒙被认为是思考20世纪中国问题的一种切入方式,若就具体思想发生及行进而言,启蒙主义更注重过程:“启蒙”是个动词,过程本身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对一代先驱者而言,他们对启蒙的结果并没有太过清晰的估量,反之,启蒙在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呈现出的更多是面对纷繁芜杂的中国社会问题时的无力感、无效感。进而言之,诚如现代性概念之滥用,启蒙是个笼统且又相当抽象的概念,这样一个主义式的概念确乎不能解决一揽子社会问题,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问题显然更为具体、迫切、坚硬、棘手,直至触目惊心、骇人听闻。也就是说,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从不缺乏传统文人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家国理想,不缺乏中国士大夫为国为民的献身理想,甚至鲁迅一生对之做出了重大坚守。至于“首在立人”“掊物质而张灵明”“拿来主义”及后来的个人主义、铁屋中呐喊也都属于思考方式或技术路线。这些方法论与世界观往往相互交杂而几乎难以辨析。对棘手的社会问题,鲁迅的启蒙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份出色的路线图,遑论科学主义话语兴起之际的科学论证。这也透露出启蒙中国总是偏于感想、理想、思想和抽象,偏偏最缺少一份出色的实践。在稍后更加务实、目标清晰、行动有力的革命时代,启蒙话语遂轻易地退居幕后。这也是鲁迅一生拒绝当导师也拒绝给青年开书单的原因:他发现了太多的中国问题与相应的治理危机,他忧心并提出了如此巨量的问题,而发现实际能得到解决的寥寥无几。对于引导年青一代知识分子治国平天下与积极治理中国问题,鲁迅严重欠缺底气;鲁迅终其一生也没有为这些问题开出过几张药方,而一般导师的重任恰在于巧引善诱。这样一位不开药方而只“引起疗救注意”的人又怎么去当一位合格的导师呢!
本著探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摩登话语。启蒙之后,对中国文学影响最深的固然是革命话语,但若细究之,则百年文学的抒情几乎深入肌理,而摩登话语最大限度启迪了中国世俗人生的现代审美、生命、消费与生活意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界对摩登话语研究多见力作,吴福辉、解志熙、陈思和、李今、陈建华、张勇等学者的论著从多个方面对摩登话语/主义做出了重要推进,其中,现代中国时期的海派文学是研究重点。在海派文化与文学研究方面,李欧梵的名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极具代表性。该著作将海派文化作为观照海派文学的大前提,极为丰富地展示了海派文化的生成空间,其中所谈上海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文化创造、出版业、商业消费、文娱活动及都市闲人对海派文学的影响都极富创见。李欧梵尽管在文献史料上多有发现,受文化研究影响的都市文化拓展也新见迭出,但仍忽视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中国科技发展对市民日常生活的巨大影响。与之相较,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中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包括科技、现代城市建设、工业生产、新式交通、公寓生活、生理卫生等在内的新科技影响下的都市市民生活做出了生动的叙描,此类还原别开生面,小说读来真实可感、可信。这些科技力量也是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穆时英的小说写作中一再呈现的对象。到了沦陷时期,摩登话语遭遇“低气压的时代”。在20世纪30年代声光化电式的呈现之后,世俗生活遭遇乱世折磨的危机成就了苏青的自叙传写作,在一个忧惧困窘的时代里谋生之艰、世态之炎凉、生命之可怖被叙写得相当真切。本著谈苏青也为破解一个谜团:张爱玲创作上的巨大光环绝不应该遮蔽了苏青的独特性。现代中国以来著名学人、作家钱锺书在沦陷时期的上海开始创作小说《围城》,小说写就十之七八之际,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很快胜利了。1945年8月之前的《围城》创作大体沿着海派文学摩登调、俏皮风、游戏感与欲望文学的路子走,可抗战胜利促使钱锺书很快启用自己所熟稔的存在主义等人本主义文学思想来匆忙填补和扭转海派惯常的摩登写作风。所以,我们看到《围城》最后十之二三部分多见严肃的人生启示。此类摩登话语在20世纪40年代的多维多面发生同构了现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
如果从王德威在其名著《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中所言海派文学传统来考察,摩登话语的行进方向着实大有可观。张爱玲一生写作断不离民国上海中心,上海在张爱玲笔下具体化为电影院、林荫大道、舞厅、购物商场、有轨电车、游乐园、跑马场、公园、现代医院、艺术教育设施、公寓生活、美食美妆等现代新式生活场景,新的科技让上海人步入现代文明的生活形态。《爱憎表》再现了张爱玲对上海的物质欲望、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生命意识觉醒与生活上的满足,而民国上海的摩登景观就此作为遗韵与遗恨走向了晚期美居时期的张爱玲那里,张爱玲的晚期写作使民国叙事内涵与质感大大强化。相较而言,王安忆在其名著《长恨歌》中绘制了一场上海摩登颓靡调的跨时代传承图景,勾勒了一个年轻女子不顾廉耻,就像变色龙一样游走于每个时代并志得意满而毫无反思的心态。同样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叶兆言在其近作《刻骨铭心》中,对民国南京的欲望颓靡进行观察时,不顾南京历史至暗时刻里的惨烈而过于夸饰欲望颓靡与醉生梦死的日常化。这些都必须做出深刻反思。
在笔者的观察中,摩登主义并不完全造就了欲望颓靡世界,实则在“荒淫与无耻”之外仍有“严肃的工作”且多有正确的人生、人性启示。考以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丰富的革命文学写作、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走向文学主流,即使在20世纪末以来的民国叙事中,革命作为“严肃的工作”的呈现仍极具砥砺中华民族气节与中国人民爱国主义情怀的重大功用。《雁城谍影》《纪念碑》的写作真正再现了历史的丰碑,一群沉浸于青春、幸福、爱与美的浪漫岁月中的男女青年,在遭遇抗日战争后沿着中华民族历史道路前行,在浴血荣光的生命陨落过程中让中华民族获得了新生。就此而言,民国摩登颓靡腔调着实应该停歇了,也真的该走一条重返民国叙事的正确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