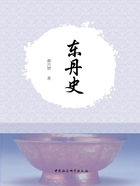
二 大延琳之叛
大延琳(? —1030),渤海国建立者大祚荣的裔孙,[59]东丹遗裔。辽圣宗时任东京舍利军详稳。太平九年(1029),大延琳于渤海灭亡百余年之后在东京辽阳发动了一场反辽复国的大起义,坚持斗争达一年之久,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次起义的原因,就是辽朝统治者对东京渤海人政治上的压迫、奴役及过重的经济盘剥直接引发的。东京辽阳府是东丹遗民渤海人集中居住的地方,渤海人与契丹政权之间因存在着灭国之仇,所以一直充满抵触的情绪。东丹国号取消后,辽朝统治者对迁居东京的渤海大族始终存在着防范心理,监督较严,平日甚至连渤海人传统的击马毬活动都受到严格限制。辽初将东丹国民南迁,为了安定民心,出于权宜之计,辽东之地“未有榷酤盐曲之法,关市之征亦甚宽弛”[60]。这种制度延续了将近百年之久,但到了圣宗太平年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等不顾历史传统和当地民情,强行改革赋税制度,“将燕地平山之法”推行到辽东渤海人居住区,致使当地渤海人负担加重,“民不堪命”。时值燕京之地连年发生饥荒,户部副使王嘉献计于朝,命辽东谙海事者造船,海运辽东之粟以赈燕民,结果是“水路艰险,多至覆没。虽言不信,鞭楚搒掠,民怨思乱”[61]。大延琳正是利用这次渤海人民怨沸腾的机会,发动了反辽复国的起义。
太平九年(1029)八月初三,大延琳于东京起兵,囚禁了东京留守驸马萧孝先(圣宗钦哀皇后之弟)和南阳公主(圣宗第四女),杀户部使韩绍勋、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德,占领东京。大延琳自立为王,建国号“兴辽”,年号“天庆”(有的文献亦记作“天兴”),“并擢辽东诸县渤海之勇谋者,置之左右”[62]。
起事之初,大延琳组成了核心的领导班子,以大延定为太师,高吉德为大府丞,刘忠正为行营都部署。地方要津亦派亲信者镇守,如命大翰庆为宁州刺史,李匡禄为郢州刺史,以南、北两面拱卫辽阳。当时得到了附近渤海人的积极响应,聚众数万,声势大振。为了扩大起义军的势力和影响,大延琳与副留守王道平共同谋划,遣使前往黄龙府联络其守将黄翩,希望能得到黄龙府方面的支持和响应。又派使者东往保州,与保州渤海人夏行美联系,企图说服他率部反辽。夏行美当时任保州渤海帐司太保,总领保州地方的渤海军。保州在今朝鲜新义州和义州之间,大延琳之所以派人策反保州,是因为希望夏行美能够取代驻守保州的军帅耶律蒲古,从东面策应辽阳起义。遗憾的是,大延琳北面、东面的策反活动都未能奏效。王道平首先背叛大延琳,弃其家从城中逃出,与派往黄龙府的使者一起向正在庆州秋猎的辽圣宗告密。辽朝掌握了辽阳城中的底细,及时地调兵遣将。国舅萧匹敌(萧恒德之子)的治地邻近大延琳,即先率本部兵马及家将占据要塞,断绝大延琳西渡之路。保州的夏行美囚禁大延琳的使者并向耶律蒲古告密,蒲古立即将保州响应大延琳的800名渤海兵全部斩杀,切断了大延琳的东进之路。
大延琳得知东、西两面都已没有出路,即分兵向北进攻沈州。因沈州副使张杰声言欲降,故大延琳没有急攻,致使沈州方面得到喘息机会,做好防御,起义军攻沈州不克,只好撤回辽阳。当年九月,大延琳遣大府丞高吉德前往高丽,请求高丽出兵攻打鸭绿江东岸的辽军。高丽应邀出兵,结果被辽军败回。[63]当时地处辽南的女真人及海州、宁州、渌州等地的渤海人都纷纷起兵响应,声援大延琳。
十月,辽朝派南京留守萧孝穆(圣宗钦哀皇后之兄)为都统,国舅萧匹敌为副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率诸路兵马进讨大延琳,起义政权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双方先后战于蒲水和手山(今辽阳南之首山),大延琳的军队连连败北,只好退守辽阳。十二月,为了打破被动局面,大延琳命大延定“引东北女真与契丹相攻”[64],并再次遣使高丽,请求支援。高丽君臣认为,“兵者危事,不可不慎,彼之相攻,安知非利我也!”[65]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作壁上观,不肯出兵相助。不久,辽军开始围攻东京城。
萧孝穆对起义军的统治中心辽阳采取的是“围城法”。“去城四面各五里许,筑城堡以围之。”[66]“筑重城,起楼橹,使内外不相通。”[67]至太平十年(1030)三月,辽阳已粮尽援绝,“城中撤屋以爨”[68]。被囚禁的驸马萧孝先与其妹趁看守者懈怠,从城中钻地道逃出,唯南阳公主在后,被守城义军发现,未能逃脱。大延琳坚守辽阳孤城至八月,其部下杨详世叛变,夜开南门纳辽军,城破,大延琳被擒,其他各城也相继投降,坚持一年之久的反辽起义终于被辽朝镇压下去了。
这次起义之所以失败,除了大延琳本人在指挥上犯了某些错误之外,最主要的是当时正值辽王朝全盛时期,有足够的力量来消灭地处一隅的起义军。但这次起义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迫使辽朝统治者对渤海人的统治做了某些政策上的调整。
第一,对渤海人进行分化,在起义中站在朝廷一边的渤海贵族给予升迁和奖赏。太平十年(1030)十一月,“诏渤海旧族有勋劳者叙用”[69]。告发大延琳的渤海人夏行美“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锡赍甚厚。明年,擢忠顺军节度使”[70]。
第二,将东京渤海人迁往中京道和上京道,削弱辽阳一带渤海人的势力,如海州,“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坚守,经岁不下。别部首长皆被擒,乃降。因尽徙其人于上京,置迁辽县,移泽洲民来实之。”[71]渌州,“大延琳叛,迁余党于上京,置易俗县居之。”[72]上京道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迁于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属置焉。”[73]看来当时辽朝迁徙辽东的渤海人还不止一次。上京道的迁辽县、渤海县,都是大延琳起义被镇压后迁辽东渤海人设置的。迁往中京道的辽东渤海人主要被安置在来州所属的迁州和润州之境。如迁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归州在今辽宁省盖州市西南归州镇;润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置州”,所属渤海县,“本东京城内渤海民平,因叛移于此。”[74]宁州治所在今辽宁盖州市九寨乡五美房村古城。宁州和归州都是东丹国南迁时所置之州。圣宗统和末伐高丽,以所俘渤海降户复置,其居民基本是渤海人。
第三,免除东京地区过多的土地税和商税、徭役,“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75]。
第四,被迫放宽对东丹遗民的某些不合理限制。如萧孝忠(应为萧孝惠,钦哀皇后幼弟),兴宗重熙七年(1038)为东京留守,“时禁渤海人击毬,孝忠言:‘东京最为重镇,无从禽之地,若非毬马,何以习武?且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分彼此?宜弛其禁。’从之。”[76]马上击毬是渤海人传统的体育项目,此后对东丹遗民的打马毬运动不再加以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