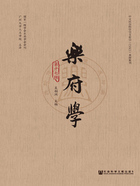
关于乐府歌诗研究的几点思考
赵敏俐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尊敬的各位先生,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在这里给我安排一个发言的机会。我讲几个问题,供大家参考,请同仁们批评。
首先,我想谈一谈乐府歌诗的概念问题。我们这个团体叫乐府学会,我们研讨会的题目一直有两个,一个是乐府学会的年会,现在是第三届;另一个更早的名称是“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目前已经是第六届了。之所以把乐府和歌诗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乐府学相对来说是概念更为明确的范畴,而歌诗的范畴相对来说要宽泛一些。不论是乐府还是歌诗,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清晰的思考和明确的界定。“乐府歌诗”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乐府歌诗,一般讲就是以郭茂倩《乐府诗集》为主,还有一些扩展。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把它称之为乐府诗,还建立了乐府学。郭茂倩《乐府诗集》收录从汉代到唐代被他称之为“乐府”的诗,这是最狭义的“乐府诗”范畴。再将其扩展些,如汉唐以来与乐府诗有关却没有被收入《乐府诗集》中的作品,特别是宋代以后的一些作品,也可以纳入“乐府学”研究的范围中来。这是狭义的“乐府歌诗”概念。而广义的“乐府歌诗”则应该从“乐府”这一国家礼乐机构的建设及其功能的角度入手考虑。我们知道,根据出土文献和相关记载,“乐府”这一机构,早在秦代就已经出现了,然而大规模地把乐府当作有影响的礼乐文化机构来建设,还是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的。但是到了西汉末年汉哀帝罢乐府,一直到东汉以后,“乐府”这一名称,就再也没有作为国家礼乐机构正式出现过,但是“乐府”这一名称却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古人为什么把“乐府”这个概念传承下来了呢?原因就是自汉武帝扩充乐府功能之后,赋予了“乐府”特殊的文化功能。“乐府”不仅仅是一般的歌舞艺术表演,实际上承担着礼乐文化建设的作用。如果从这一角度来讲,我们在讨论乐府学作为“乐府”二字的文化本质时,就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因素,它不仅仅是文学的研究范畴,其实还和国家礼乐文化建设相融合。从这一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需要把“乐府歌诗”的研究范围做更大的拓展。中国从周代社会开始,就特别强调礼乐文化建设,周代社会的乐官机构就是汉武帝时代的“乐府”的前身,二者在国家的礼乐文化建设方面有着共同的职能。而周代礼乐文化留传下来的主要文献就是《诗经》,《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颂”就是宗庙乐歌,“雅”就是朝廷的乐歌,“风”就是各地的世俗民情的乐歌。如果按照“风”“雅”“颂”的分类来看,汉代以后的乐府,包括郭茂倩《乐府诗集》收集的乐府诗,基本上不出这三大类。朝廷的、宗庙的祭祀乐章,在《乐府诗集》中是第一部分。接下来就是文人的一些创作,关乎国家政治兴衰的一些乐府诗,还有表达世俗民情的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把“乐府歌诗”的概念扩展到先秦时代包括《诗经》在内的“乐歌”,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乐府歌诗”的发生发展及其艺术本质做出探本溯源的研究。而这也正与我们最早使用“歌诗”这一概念的初衷一致,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建构“乐府歌诗”的研究体系。这和我们所要追求的学术目标有直接关系,和我们建立乐府学会的宗旨有直接关系。
其次,乐府学会和乐府学、乐府歌诗的学科归属问题。我们现在所做的乐府学研究,从我和吴相洲老师一开始做这方面的学术探索的时候,当时提出的是“歌诗”的概念。我们第一次会议的名称是“中国诗歌和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后来提出了“歌诗”的概念,又提出了“乐府”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乐府学和歌诗的研究应该是综合性的艺术类的学科,而不单单是文学学科。因为我们首先要考虑到音乐学方面的问题,要考虑到语言学方面的问题,还有礼乐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学科的划分都比较细致,在文学院内部,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更有甚者分为先秦文学、唐宋文学、元明清文学,互相之间都不太来往。这样的话就影响了乐府学的发展,因为乐府学和歌诗研究不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和吴相洲老师当时就有了明确的想法,我们应该和音乐学界的学者一起,共同探讨。基于这样的认识,前几次会议,我们邀请国内外著名的从事音乐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如赵宋光先生以及音乐学院的诸位同仁。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合作友谊,如多次参会的李健正先生,一直特别支持我们。我觉得在李健正先生、项阳先生、李玫先生等诸多音乐学界的同仁支持下,使得我们乐府学会不再是单纯的文学研究机构,而是和音乐学家一起做的工作。所以从学科的归属来讲,乐府学应该属于交叉学科,或者称之为综合学科,如果更准确地说,可以把乐府学称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现在的情形是,参加我们会议的基本上还是以文学研究者为主,论文集中讨论的问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在以文学研究为主的基础上,向音乐学扩展。涉及一些礼乐制度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音乐学、没有从事礼乐制度研究者的参与,想要把乐府学作为当代显学,还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希望以后开会的时候,能够邀请相关学科的学者参加我们的会议,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再往外走一步,多做一些扩展。就我个人而言,想和音乐学界的学者一起进行交流,现在还有一些困难。首先就是学科的局限,对音乐学界不太了解,有时候很难请到相关学者。我们之前下了很大力气邀请中国文化艺术研究院、中国传媒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的学者,但这些联系建立的还不够广泛。我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建立更多的联系,也希望项阳老师、李健正老师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支持。这一点特别重要。还有一点,在会议研讨过程中,往往是音乐学家有一套话语体系,文学研究者另有一套话语体系,虽然参加的是同一个会议,但有时候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如何才能开展深层次的交流,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些相关的课题一起来做。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最后,乐府歌诗的研究方法和目标。我们主要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的多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思路不是特别开阔。吴相洲老师在这方面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比如他把乐府学划分为三个方面:文学、音乐学、文献学研究。在这三个大的研究层面上,又分为八九个具体的研究方向,这在这些年来乐府学研究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很多学生的毕业论文、会议论文都是按照这个体系来做的。如果再往下发展的话,我想还是应该再做一些扩展,既然乐府学不属于单一的文学学科,也不仅仅是文献学、音乐学学科,而是一个综合学科,我们就应该进一步考虑这一学科的特点,要考虑我们研究乐府学、研究文学和音乐学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最后阐释的关键在哪里。举例来讲,比如我们要研究汉乐府《陌上桑》,要弄清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光靠文学的研究是不行的。过去人们解释这首诗,大多都认为这首诗说的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太守,看见了一个美丽的采桑姑娘,就要调戏她,而采桑姑娘义正辞严地拒绝他的故事。这种阐释方式基本上就是文学的阐释,而且是带有鲜明的具有时代色彩的政治思想阐释,这个阐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和阐释杜甫的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站在文学的角度讲,这一解释也是有道理的,而且很符合近百年的文化思潮。但是光有这种阐释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从音乐的角度再仔细想一想。根据文献记载,《陌上桑》这首诗当时是用来歌唱表演的,而不仅仅是纯粹的一首文学作品。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歌辞只不过是这个表演艺术的文字写本,并不是它的全部。它属于“清商三调”中的一曲,它的表演程式很复杂,至少有七八种乐器参与,全诗分为“三解”,亦即三个段落。由此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过去把《阳上桑》当成是一首简单的民歌的说法可能是有问题的。根据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清商三调的表演场合来看,它不会是出自民间的“街陌谣讴”,而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歌舞艺术团体的创作与表演,而且更大的可能是在当时的宫廷贵族和富商大贾之家的演出节目,用于他们的观赏与娱乐,是当时的“流行艺术”。由此我们就会再做进一步的追问:这些汉乐府诗在当时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它们的创作目的是什么?艺术本质是什么?我认为,乐府歌诗的研究所以是综合艺术研究,就因为乐府歌诗本身的复杂性,这就涉及我们对于这些乐府歌诗的本质的理解,需要做更深入的理论思考,这样才能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
还有一点,我们把乐府定义为礼乐文化机构,乐府诗中有很多和礼乐文化相关。它们在当代的文化建设当中有什么意义吗?我们总说中国有三千年的文明,我们是礼仪之邦,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礼乐文化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我们读《诗经》总是感叹,在周代社会竟然产生了像《鹿鸣》这样高雅而又优美的迎宾曲,在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建设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社会的流行歌曲和音乐很受人喜欢,影响也很大,但是在今天我们还缺少像《鹿鸣》这样优秀的歌诗用于当代的礼乐文化建设,是不是我们的乐府学会做一些这方面的思考。
以上所言,仅是个人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敬请批评指正,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