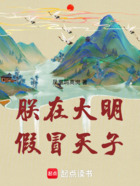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53章 赏赐和勒索
朱祁镇虽恨得牙关紧咬,心中早已将郕王与于谦凌迟了千万遍,面上却不得不扯出一抹云淡风轻的笑意,做出一副宽宏大度的模样,倒显出几分不合时宜的豁达来。
他深知,此刻若指认二人为乱臣贼子,非但于事无补,反倒会将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
一则,他尚存几分清醒,固守京师本就是明智之举,若郕王与于谦力主守城,而他这个身陷敌营的皇帝反倒主张弃都,岂非要坐实了昏君之名?
这般自毁长城的蠢事,与那亡国的宋徽宗何异?
二则,他更不愿成全了郕王的贤名,倘或自己当真背上了意欲弃都的骂名,反倒将郕王衬托得愈发有英主之姿。
这般损己利人的荒唐事,他朱祁镇岂会为之?
三则,自己之所以还能黏黏糊糊地占着皇帝的名分不放,全赖于瓦剌无资格废立,而大明亦无理由废君。
战败被俘尚不足以动摇他的正统之位,满朝上下,唯有孙太后执掌废立之权。
而孙太后既已立储,其意不言自明,她终究是盼着儿子还朝的。
倘或孙太后果真一心护持,那普天之下便再无人能撼动他的帝位。
因为自明太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度以后,大明王朝便再无权臣立足之地。
就算于谦发了大疯,甘愿毁弃数十年清誉执意废帝,满朝文武也决不会俯首听命。
此乃祖制所定,国体使然。
于谦所能为者,不过借抵御外侮之名,劝说孙太后拥立郕王,他没有任何法理依据与政治实力去直接废黜君王。
然而,若他此刻贸然指认郕王与于谦为乱臣贼子,将二人守卫京师的壮举污为谋逆之举,那便是自绝于大明。
届时,面对一个公然“投敌”的君王,朝野上下反倒有了废帝的正当理由,并能以此逼迫孙太后。
倘若当真被废,他在瓦剌的立身之本与南归回京的正当性便荡然无存了。
故而无论如何,朱祁镇都要牢牢掌握住这“正统天子”的名器,只要帝位尚在,他的一言一行在法理上便仍是“圣谕昭昭”。
纵使郕王与于谦百般推诿,顶多也只能以“虏营矫诏”相搪塞,却万万不敢公然宣称天子之言已非圣旨。
就在刘安平身的那一瞬间,朱祁镇在心中便完成了这一整套缜密算计。
待对方身形甫定,他甚至还故作从容地补上一句,“朕岂会不知于卿良苦用心?靖康之耻历历在目,他这般作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刘安闻言,顿时松了好大一口气,此番他能冒险出城面圣,全凭着一腔君臣之义,正因存着这份赤诚,他才不敢对朝中剧变有半分隐瞒。
所以他最怕的就是皇帝骤闻实情后雷霆震怒,直斥郕王、于谦谋逆,甚至否定固守京师之策,若果真如此,他刘安这个传话人夹在中间,必将进退维谷,里外难做人。
万幸,万幸,皇帝终究还是保持着帝王应有的清醒与克制。
伯颜帖木儿冷眼旁观,早将朱祁镇强忍怒意时面部细微的抽搐,与其眉宇间那一闪而逝的狰狞尽收眼底。
他略一思忖,顷刻间便洞悉了皇帝的艰难处境。
他当即堆起满脸憨笑,毕恭毕敬地向朱祁镇躬身道,“陛下说什么靖康之耻?您能驾幸我瓦剌北狩,实乃我部无上荣光。”
“我也先太师曾说,‘臣有什么本事征伐南朝?只是长生天垂怜,特赐我与天子一晤的机缘罢了’。”
朱祁镇心知,伯颜帖木儿之所以在大明臣子面前待他如此恭顺,绝非是真心要给他留什么颜面。
而是要借他这块“金字招牌”,好教大明臣子乖乖就范,所以非得营造出一种“大明皇帝甘愿驻跸漠北”的假象不可。
然而伯颜帖木儿终究低估了中原天子的威严,若在往日,朱祁镇尚未沦为阶下囚时,早该对其厉声呵斥,“朕与刘卿议事,岂容尔等置喙?”
可如今虎落平阳,眼见伯颜帖木儿贸然插话,朱祁镇只得强压怒火,勉强扯出一丝僵硬的笑意,随即别过脸去,对其假模假样的阿谀奉承置若罔闻,权当是被这塞外的风沙迷了眼。
皇帝这般隐忍作态,刘安岂能看不出其中异样?
只是眼见圣驾被瓦剌兵卒团团围困,饶是他满腔忠愤,此刻也不敢越俎代庖,替天子发作。
倒是那与也先结有姻亲的李让机敏,见场面僵持,当即打圆场道,“也先太师此言极是!陛下北狩多时,终是要南归的。”
朱祁镇又暗自思忖道,郕王想不想当皇帝暂且不论,但以他对于谦秉性的了解,他既已决意固守京师,纵使刀山火海也定会死战到底。
除非瓦剌甘愿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战机,主动退兵。
然而这些时日与伯颜帖木儿周旋下来,朱祁镇已然看清,也先此番所图非小,即便不说恢复蒙元疆土,但要让瓦剌人空手而归,将他这个大明皇帝完璧归赵,也无异于痴人说梦。
如此看来,这场恶战已在所难免。
既然战事不可避免,以他如今的处境,倒真该如伯颜帖木儿所言,趁势向刘安多多索要金银,毕竟在这漠北苦寒之地,钱财才是最实在的保命符。
何况他虽贵为天子,但若不能拿出真金白银的赏赐,这些蛮夷背地里定要讥讽他白吃白喝。
伯颜帖木儿那厮,日后怕是要天天拿这事作筏子,明里暗里地折辱于他,他岂能受这等腌臜气?
再者说,袁彬这些日子护卫左右,鞍前马后地替他操持各种苦活累活,若连些许赏赐都给不出,他这个当主子的,又颜面何存?
瞬息之间,朱祁镇已拿定主意,他一整衣襟,对刘安正色道,“朕虽北狩,然瓦剌拥朕而来,若不行赏,恐失天朝体统。”
刘安闻言立即会意,却面露难色道,“陛下,此事干系重大,臣一人恐难独断……”
朱祁镇神色一凛,沉声道,“我朝见藩属国朝贡,历来奉行‘厚往薄来’之制,也先太师早已向我大明称臣,按例当受‘赏赐’,此事何须再议?”
这话确非虚言,自大明开国以来,为彰显“天朝上国”的气度,朝廷对朝贡使节向来慷慨至极,堪称历代之最,除按值给付贡品银两外,更有丰厚“回赐”。
此制肇始于洪武时期,为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气象,朝廷不惜耗费巨资,对来朝贡的藩属国一律实行“厚往薄来”。
使臣入境后,沿途州县不仅要负责全部食宿,更要设宴款待,贡品估值后,朝廷必以数倍价值的回礼相赠。
如此“礼尚往来”,原为彰显大国风范,却渐渐沦为诸国“吃大户”的捷径,许多边远小国争相来朝,甘为“藩属”,实则皆为牟利而来。
明太祖朱元璋对此却是乐见其成,因为在历代帝王眼中,一个强盛王朝往往具备两大标志,其一是军威赫赫,战无不胜,其二则是万邦来朝,四夷宾服。
各国使节在奉天殿前行三跪九叩之礼的景象,确是能令每一位帝王都心驰神往的荣耀。
虽然这份荣耀的背后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但表面上却是宾主尽欢,异域使臣执礼甚恭,天朝君主厚赐有加,完美契合儒家“怀柔远人”的治国理念。
即便是最苛刻的科道官,对此也挑不出半分不是。
因此若论藩属国之众,大明可谓冠绝古今,历代中原王朝,强如汉唐,盛如蒙元,其藩属国最多不过数十,唯独大明,鼎盛之时竟有一百四十余国来朝。
毕竟只需呈上几份言辞谦卑的表文,在金阶下磕几个头,说些歌功颂德的漂亮话,便能换来白花花的银子,这般“稳赚不赔”的买卖,全世界恐怕都再难找出第二家了。
然而当大明军威日渐式微,对周边地区的威慑力不断衰减之时,这所谓的“朝贡”便渐渐露出了“合法抢劫”的真面目。
早在土木堡之变前,瓦剌使团就屡屡借朝贡之名,行劫掠之实,其使臣往来途中横行无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胁迫其他部落一同为祸边疆,向朝廷勒索珍宝。
稍有不满,便在边境挑起事端,朝廷虽年年增加赏赐,却始终填不满也先贪婪的胃口。
及至朱祁镇被俘,这层遮羞布便被彻底撕去,所谓“朝贡”,实为明火执仗的敲诈勒索,所谓“赏赐”,不过是花钱买一时太平的赎金罢了。
但此事关乎大明“天朝上国”的体统颜面,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道破其中玄机。
试问哪个臣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能对皇帝直言进谏,说出“所谓朝贡实为劫掠,诸国称臣只为牟利”?
故而即便也先所谓的“称臣”早已名存实亡,甚至胆大包天到俘虏了皇帝,朱祁镇仍旧一口咬定这是“天恩赏赐”而非“蛮夷勒索”。
“朝贡”二字一出,刘安顿时语塞。
因为在这一套儒家的政治话语体系里,朱祁镇已然牢牢占据了道德高地。
纵使郕王来日当真登临大宝,也绝不敢公然否认也先“称臣纳贡”的政治姿态。
倘若传扬出去,泱泱大明竟被瓦剌一边境小部勒索,岂不沦为千古笑谈?惹得四邻番邦背地里耻笑大明徒有其表?
须知天朝体统之重,远胜于府库之虚实,在这等事关国体的要务上,大明宁可以金银换体面,也绝不能失了天朝上国的威严。
所以刘安明知皇帝这是哑巴吃黄连,却也不敢点破其中原委,只得躬身应道,“陛下圣明,此事确无再议之理,只是事关府库钱粮,臣不敢专擅,恳请陛下宣召城中大小官员一同觐见,共议赏赐之事。”
朱祁镇心知刘安这是怕日后落人口实,被参个“擅动府库”的罪名,必要拉上众官作个见证,当下便颔首道,“好,准卿所奏。”
于是大同城内文武一同穿戴整齐,鱼贯出城觐见圣驾。
众臣一见皇帝,皆无不痛哭流涕,其中尤属郭登最是悲恸欲绝,“当日六军凯旋,孰料竟遭此奇祸……”
朱祁镇先前未纳郭登“自紫荆关回銮”之谏,早已是追悔莫及,眼下又见郭登哭得如此哀切,更觉其忠心可鉴,不由动容叹道,“皆因朕不听郭卿之言,致将骄兵惰,终为所误。”
又是一番君臣痛哭之后,朱祁镇目光如炬地一一扫视过跪伏在地的大同众官员,忽然眉头一皱,沉声问道,“石亨何在?为何不来见朕?莫非还在为上回朕让他戴罪立功之事耿耿于怀?”
刘安闻言,急忙叩首解释道,“石参戎(参将别称)日前已被大司马急召入京,负责重整京营防务去了。”
朱祁镇听罢,愈发觉得于谦心机叵测,却又不能明言指责,面上不得不强压愠色,故作淡然道,“原来如此,于卿当真是知人善任。”
“朕这边才稍加磨砺人才,他倒是一个不落地都要揽去,这般迫不及待地收入麾下。”
“朕前脚刚责罚了石亨,命其戴罪立功,后脚于卿便擢升其职,还调他去了京营,这般施惠上下,倒叫石亨不得不感念他于大司马的知遇之恩了。”
刘安又被皇帝的语气吓了一跳,赶忙俯首恭声道,“阳和口一役,陛下宽宏大量,未治石亨死罪,已是法外开恩。”
“石亨纵是愚钝,又岂敢忘却陛下再造之恩?大司马虽有擢用之举,终究不及陛下皇恩之万一。”
朱祁镇不阴不阳地轻笑了一声,“那便承刘卿吉言了。”
言罢,他又状似漫不经心地问道,“大同府库如今现存钱粮几何?”
郭登叩首回禀道,“库内现存白银一十四万两,不知陛下欲取用多少?”
朱祁镇略一沉吟,懒洋洋地掐指计算道,“给朕取两万两千两来,其中五千两赐予也先太师,五千两分赏伯颜帖木儿等三人,再有余下的,便散给瓦剌众将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