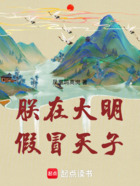
第46章 王府私军的问题
于谦见自己劝不动张祁重用成敬,不由意味深长道,“殿下如何不似汉武帝?用人如积薪,竟是后来者居上。”
张祁自嘲一笑,忽然想起在现代时听过的一个段子。
说曾经有一个大善人,常常对自己的家人说,“我心善,眼里见不得穷人,其他地方我管不了,但我家方圆十里内,绝不能有穷人。”
于是,这位大善人的手下家丁,就把大善人家附近所有的穷人统统赶走了。
原本觉得这个段子是在讥讽富人假仁假义假慈悲,而今身临其位才明白,原来这个段子里的“大善人”也未必好过。
张祁心想,本来他不知道成敬的身世倒也罢了,如今既已知晓,他就跟这个段子里的富人一样,见贫贱而心生恻隐,却又无力施为,只得眼不见为净,第一反应,就是赶走让自己难受的“穷人”。
倘或当真委成敬以重任,把他当作寻常奴婢使唤,只怕不出旬月,说不定成敬还没疯,他张祁先得精神病了。
因此,为了自己的心理健康,他决定往后在内廷给成敬安排一个清闲职位,把人舒舒服服地养起来,让他过得好一些。
但要让他把成敬升作司礼监掌印,他是真的做不到。
只是这其中的曲折心思终究不便与于谦明言,想那汉武帝、明宣宗都能毫无心理障碍地让被阉割的士大夫入侍内廷,偏他张祁畏首畏尾,踌躇难决。
这般色厉内荏,岂非坐实了他不过是个纸老虎?
为了不被于谦当作纸老虎,张祁当即便回道,“昔年汲黯谏汉武帝言‘后来者居上’,原是因他恪守论资排辈之制。”
“彼时汲黯高居九卿之位,公孙弘、张汤尚不过微末小吏,然此二人因政绩卓著得以擢升,终至位列三公、爵封列侯,反居汲黯之上。”
“而公孙弘之辈外饰儒术而内怀诡诈,曲意逢迎以媚君上,张汤之流则专务刀笔之能,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刑狱为晋身之阶。”
“故而汲黯所谓‘后来者居上’,实乃讽武帝重用酷吏之弊,而今本王麾下既无张汤之流以罗织为能,亦乏公孙弘辈以谄媚为事,少司马此言,未免有失公允。”
于谦闻言笑了一笑,转开话锋道,“郕王府的王府官中其实藏龙卧虎,只是殿下未曾慧眼识珠罢了。”
张祁摇了摇头,“汉武帝坐拥百万雄师,而本王连府中护卫都调动不得,何来可用之人?”
这是张祁在成为“假郕王”后,才发觉的一个严重问题,历史上的景泰帝为郕王时,是根本调不动一兵一卒的。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分封诸王时的规定,亲王麾下理应拥有指挥三员,千户、百户各六员,为亲王统领“三护卫”,加上六百七十二名正旗军,专司王城戍卫,亲王的入朝,更是可以随侍马步旗军,不拘数目。
在调兵机制上,朝廷与亲王形成双重制约,守镇官发兵必须同时获得御宝文书与亲王令旨,遇有警急,亲王更可统一节制辖区内所有驻军,除此之外,每年冬春之际,亲王还可通过出猎来演武练兵。
然而,这一套由明太祖精心设计的藩王军事制度,在永乐、宣德年间便彻底名存实亡。
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夺位后,深谙藩王掌兵之害,遂逐步剥夺诸王兵权。
他通过一系列措施,将诸王排除在军事指挥体系之外,即便遇有战事,朝廷也只征调王府护卫,而亲王本人则完全丧失了洪武时期的军事主导权。
不过朱棣在削藩的过程中,却始终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网开一面,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不仅保留了王府护卫,更享有实际军事指挥权。
后来汉王叛乱时,虽然其勾结朝臣的图谋未能得逞,但朱高煦依旧凭借祖制赋予的“王府三护卫”,得以成功集结兵马发动叛乱。
因为根据祖制,亲王王府护卫指挥、千百户等武职虽可世袭,却需先由亲王核准世袭资格,然后再遣专人持令赴京报备。
尤为关键的是,亲王在王府武官选用上也享有特殊权限,按规定,亲王可直接从所辖军职中选拔千户、百户等武官,只需将人选履历亲署奏本,不经任何衙门中转,直呈御前审批。
这种“专折奏事”的特权,使得亲王在军事人事上保有相当自主权,其选拔的武官更享受与京官同等的俸禄待遇。
因而朱高煦起兵时,即便面对朝廷的绝对优势,他仍能通过对护卫军官施以私恩,以维系“三护卫”对自己的忠诚。
但这一赋予亲王组建私人武装的制度空间,至宣德朝已荡然无存。
明宣宗以更为隐蔽而系统的手段完成了对亲王军权的剥夺,他通过“征补护卫”与“复府军卫”两项政策,以温水煮蛙的方式实现了对王府护卫制度的釜底抽薪。
在具体操作上,朝廷以补充都司卫所兵员为由,逐步抽调王府护卫,同时暗中运作,授意王府官军“主动”奏请回归原卫所。
这套组合拳下来,虽然“王府三护卫”的职衔名目犹存,但其实际兵员已被整体划归地方卫所统辖,亲王与这些名义上的护卫已再无统属关系。
这一变革又产生了另一个连锁反应,随着王府护卫制度的实质消亡,亲王对王府武官的管辖权也随之被一应剥夺。
即便发现王府武官有不法行为,亲王既不能自行治罪,更不得滥用刑罚,必须奏请朝廷处置。
所谓“前人种因,后人食果”,景泰帝朱祁钰正是这一历史因果的典型受害者。
如果历史上的景泰帝在潜邸之时仍能保有祖制赋予的“王府三护卫”,拥有一支由指挥使、千户、百户层层统属的嫡系亲军,那么“夺门之变”的结局将会改写。
在明英宗即将复辟的危急时刻,如果有一支忠诚的郕王府亲卫军据守宫门,构筑防线,即便不能完全阻遏政变,也起码能为景泰帝赢得调兵勤王、召集大员的宝贵时间。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当石亨率领的叛军冲破宫门时,偌大的紫禁城内竟无一支真正效忠于景泰帝的武装力量,于是只能坐视权柄易手。
而张祁则是明初削藩政策下又一个被历史车轮碾过的牺牲品。
倘或朱祁钰原先就能如洪武旧制般蓄养府兵,那么张祁便能继承一支建制完整的王府护卫军。
虽不敢奢望这支亲军能成什么大事,但至少能让他获得基本的安全保障,譬如宫门戍卫可交由亲信千户,贴身防护能托付世代效忠的百户家将,无论如何总会多点儿安全感。
何至于像现在这般如履薄冰,连身家性命都要仰仗张輗、张䡇兄弟在禁中庇护?
更令张祁无语的是,明宣宗将王府护卫划归地方卫所统辖后,依照于谦先前所科普的大明军制,他的王府护卫须经天子敕令、兵部调遣方能调动。
换言之,即便他张祁是真郕王,若想要调动本该属于自己的王府护卫,也得先问过于谦才行。
因此,于谦远比张輗、张䡇兄弟淡定得多,他压根不担心张祁会反客为主。
毕竟,论及兵权,于谦其实才是他们四人之中,唯一一个由朝廷法度认可的调兵实权者。
只是于谦此人颇具君子之风,并没有在张祁面前耀武扬威,此时听得张祁抱怨调兵之难,不过淡然一笑,从容进言道,“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遂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重用酷吏,殿下若能礼贤下士,宽恤民下,赏罚无失,纵无兵权,又何患之有?”
张祁心想,拉倒吧!汉武帝虽被诟病穷兵黩武,却稳坐帝位五十四载。
而历史上对你言听计从的景泰帝却区区八载便被废黜,这不正是兵权旁落的血泪教训么?
但眼下并不是与于谦争论王府亲卫军兵权归属的时候。
张祁心知,以于谦那等公而忘私的秉性,纵使他此刻当真握有王府亲卫,于谦也必定会劝他将这支劲旅献出,以解北京保卫战的燃眉之急。
于是张祁含蓄一笑,权作从谏如流之态,“既如此,不知郕王府中,尚有何等卧虎藏龙之辈可堪大用?”
于谦略一沉吟,如数家珍般道来,“王府左长史仪铭、右长史杨翥、审理正俞纲、殿下的伴读俞山、另有现任户科给事中王竑,皆可委以重任。”
张祁闻言,眉峰微蹙,难掩讶异,“王竑竟也是郕王府的潜邸旧臣吗?他不是正统四年己未科的进士吗?那他后来怎么当上的户科给事中?”
于谦正色道,“殿下有所不知,此乃我朝观政进士之制,昔年太祖皇帝见唐宋科举但重词章,元代取士多夤缘请托之辈,故而特创此制。”
“依祖制,鼎甲及前列进士多直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或授承敕监中书舍人,可不经观政,余者方需经历观政历练,方可得授实职。”
“观政进士所历衙门,皆是朝廷机要所在,六部之中,吏部铨选、户部钱粮、礼部仪制、兵部军务、刑部律法、工部营造,各有专司,都察院监察百官,大理寺平决刑狱,通政司掌受章奏,皆是历练要地,就连五军都督府这等军机重地,亦在观政之列。”
“观政之时,观政进士须研习《大明律》及诸司则例,以通晓政务根本,更要随堂官外出办差,实地习练政事处置,每逢乡试之年,多充任同考官,既察士子文章,亦习科举规制,平日还需草拟奏章、参议朝政,以此培养审时度势之能。”
“然至永乐初年,因取士日众而官缺有限,遂有变通,除前列仍入翰林外,余者或留京观政,或分派诸王府为辅佐,更有悉遣归进学者,此为权宜之计,非祖宗定制。”
“及至永乐末年,又有新例,进士及第者多授行人司行人之职以观政,可见这观政之制,实乃因时损益,随国朝所需而变。”
“说来惭愧,下官当年亦是在行人司观政历练,后蒙圣恩擢为御史,而今王竑能在郕王府脱颖而出,其才具之出众,可见一斑。”
张祁暗自盘算着时间线,忽觉其中似有蹊跷,“少司马乃是永乐十九年辛丑科进士,至宣德元年方授御史,前后历时五载。”
“而这王竑,是正统四年己未科的进士,至正统十一年才得授户科给事中,竟历七载之久,这观政之期,怎有如此参差?”
于谦答道,“太祖旧制,原定观政三月即可授官,然近年来进士取录日众,而诸司官缺有限。”
“故而近年所取进士中,第三甲多以王府教授、伴读之缺观政,仍食八品俸禄,二甲、三甲仅留七十员分隶诸司观政,遇缺取用,余者皆遣归进学。”
“故而观政五载乃至七载方得授官者,实为寻常,与王竑同科登第者,至今仍有不少人候缺待职,未能实授,此乃时势使然,非才学之过也。”
张祁一下子就明白了。
这不就是现代的“学历贬值”吗?
随着社会发展,和平年代的繁荣让人才变得不再稀缺,内卷愈演愈烈。
明朝官场大抵也是如此。
国初草创,人才匮乏,区区举人即可出仕州县,一介进士便堪主政一方。
然承平日久,朝廷取士愈众,而实缺愈稀,纵是两榜进士,亦不免蹉跎岁月,即便金榜题名,亦难逃候补待缺之苦,致使莘莘学子虽皓首穷经,终难逃“怀才不遇”之叹。
这么一想,成敬的遭遇则更显凄凉,倘若他不是在宣德年间入仕,而是赶上靖难之役后朝廷急需用人之际,或许就能免遭腐刑之祸了。
张祁默默感叹了一回,方收回思绪,道,“那既然如今朝廷官缺是僧多粥少,按理说该有大批士人争相入我郕王府效力才是,可眼下府中堪用之人寥寥,这却是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