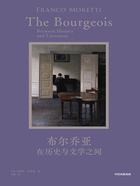
导论:概念与矛盾
一、“我是布尔乔亚阶级的一员”
布尔乔亚(The bourgeois)……不久以前,这似乎还是社会分析不可缺少的概念;现在,人们可能好多年都没有听到有人提起它了。资本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力量,但它的人类化身却似乎已经消失了。“我是布尔乔亚阶级的一员,我能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布尔乔亚,而且我历来生活的氛围就使我具有布尔乔亚的观点和理想”,1895年,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写道。[1]今天谁还会重复这些词句呢?布尔乔亚的“观点和理想”——那是[2]什么?1
氛围的变化反映在学术作品中。西美尔(Simmel)和韦伯,桑巴特(Sombart)和熊彼特(Schumpeter),他们都把资本主义和布尔乔亚——经济和人类学”——视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25年前,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写道:“关于我们的这个现代世界,如果没有……布尔乔亚什(the bourgeoisie)[3]的概念,我不知道能有什么严肃的历史解释。这么说有着充分的理由。人们不可能讲一个没有主人公的故事。”[4]然而,甚至那些极度强调“观点和历史”在资本主义崛起中的作用的历史学家”——梅克辛斯·伍德(Meiksins Wood)、德·弗里斯(de Vries)、阿普尔比(Appleby)、莫基尔(Mokyr)”——都对布尔乔亚的形象鲜有或没有兴趣。梅克辛斯·伍德在《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里写道“:英格兰有资本主义,但它并不是由布尔乔亚什创造的。法国有(某种程度上)取得了胜利的布尔乔亚什,但它的革命方案同资本主义没什么关系。”或者,最后:“布尔乔亚……与资本家(capitalist)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同关系。”2[5]
确实,没有必然的等同关系;不过,那并不是要点所在。“布尔乔亚阶级及其特质的起源”,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写道,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与资本主义劳动组织的起源问题无疑是密切相关的,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6]密切相关,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这是支撑着《布尔乔亚》的观念:把布尔乔亚与他的文化”——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布尔乔亚确定无疑地是一个“他””——视为一个权力结构的其中两个部分,然而它们与这个结构又并非简单地重合。但是,对“这个”单数形式的布尔乔亚的谈论,本身就问题重重。“大布尔乔亚什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霍布斯鲍姆(Hobsbawm)在《帝国的年代》里写道,“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7]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补充说,这种可渗透性,使布尔乔亚得以区别于
在它之前的贵族和在它之后的工人阶级。这些对比分明的阶级尽管各有其显著的特点,但在结构上它们有更为突出的同质性:贵族通常是由政治爵位结合司法特权构成的法律地位规定的,而工人阶级则主要接受的是体力劳动条件的界分。布尔乔亚什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没有可与它们相比的内在统一性。[8]3
疏松的边界,虚弱的内部凝聚力:这些特征取消了将布尔乔亚什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待的观念吗?对于在这一问题上最伟大且仍健在的历史学家于尔根·科卡(Jürgen Kocka)来说,未必一定如此,只要我们区分出我们会把什么称作这一概念的核心,又会把什么视为这一概念的外围。后者事实上是极其多变的,无论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历史层面上;一直到18世纪,它主要由欧洲早期城市中“那些个体经营的小商业者(手工业者、零售商人、旅馆业者、小店主)”组成;一百年后,组成它的是完全不同的人口,即“中低等级的白领雇员和公务人员”。[9]但与此同时,在19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有资产且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什”的融合形象在西欧出现,为整个阶级提供了重心,并强调它有适于作新的统治阶级的特性:这二者的会聚在德语的一对概念中找到其表达”——Besitzs-和Bildungsbürgertum,即资产的布尔乔亚什和文化的布尔乔亚什,或者用更平淡的说法,这二者的会聚在英国的税收体系中找到了表达,这一体系将(来自资本的)“利润”与(来自专门服务的)“报酬”一视同仁地放置“在同一个表头之下”。[10]
资产与文化的相遇:科卡的理想型(ideal-type)也将是我的理想型,但有一个重大的差别。作为文学史家,我关注的焦点将不放在特定社会群体”——银行家和高级公务人员,实业家和医生,等等”——之间的现实关系上,而在文化形式与新的阶级现实之间的“贴合”中,例如,像“舒适”(comfort)这样的词语怎样勾画了资产阶级正当消费的轮廓;或者,讲故事的节奏如何适应新的生活规则。从文学棱镜中折射出的布尔乔亚”——这是《布尔乔亚》的主题。4
[1]“Der Nationalstaat und die Volkswirtschaftspolitik”, in Gesammelte politische Schriften,Tübingen 1971,p.20.[译注]中文译文见马克斯·韦伯著,甘阳选编,甘阳等译:《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02页。莫莱蒂将韦伯文中的Bürgertum译为bourgeois class,将Bürger译为bourgeois,为贴近莫莱蒂这样的用词,这里将甘阳译文中的“市民”全部替换成了“布尔乔亚”,虽然从德文的角度说,“市民”是一个更准确的翻译。在德语中Bürgertum和bourgeois“存在细微的,但很显著的差别”,Bürger“既是一个法律概念,又是一种社会标签:它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国家的公民或一个阶级的成员”(彼得·盖伊著,赵勇译:《感官的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9页)。在下文与这些概念的相关措辞中,在莫莱蒂对德文作英译的地方,中译将仍尊重莫莱蒂的用词而对中文里的已有表述进行调整,在莫莱蒂保留德文原词的地方,将按照中文已约定俗成的翻译,把Bürgertum译为“市民阶级”,把Bürger译为“市民”。本书以下部分,凡引文有中文译文,都会尽量采用已有译文并给出译文出处,但也会根据满足莫莱蒂论述的语义与修辞需要作适度调整,不再另作说明。
[2]原文为斜体,表强调,在本书中均用黑体表示,下同。
[3][译注]Bourgeoisie与bourgeois为同根词,前者为集合名词,后者作名词时为个体名词。如果意译,一般会把前者翻译为“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把后者翻译为“资产阶级分子”“资产者”或“市民”。本书用音译的方法翻译这一组词语,并从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翻译中借用一种区分的方式,将前者翻译为“布尔乔亚什”,将后者翻译为“布尔乔亚”。
[4]Immanuel Wallerstein,“The Bourgeois(ie) as Concept and Reality”, New Left Review 1/167(January-February 1988),p.98.
[5]Ellen Meiksins Wood,The Pristine Culture of Capitalism:A Historical Essay on Old Regimes and Modern States,London,1992,p.3;第二句话摘自The Origin of Capitalism:A Longer View(《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个更长远的视角》),London 2002(1999),p.63。
[6]Max Weber,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New York,1958(1905), p.24.[译注]中文译文见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5页。
[7]Eric Hobsbawm,The Age of Empire:1875—1914,New York,1989(1987),p.177.[译注]中文译文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这里根据莫莱蒂论述的需要有改动。
[8]Perry Anderson,“The Notion of Bourgeois Revolution”(1976),in English Questions, London, 1992, p.122.
[9]Jürgen Kocka, “Middle Class and Authoritarian State: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German Bürgertum in the Nineteen Century”,in his Industrial Culture and Bourgeois Society. Business,Labor,and Bureaucracy in Modern Germany,New York/Oxford,1999,p.193.
[10]Hobsbawm,Age of Empire,p.172.[译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贾士蘅译:《帝国的年代:1875—1914》,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