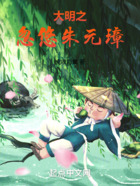
第77章 归宗
夜色如漆,弯月如钩,大环村半山腰的祠堂里火把忽明忽暗,张寒山上下打量着张仨,不知何时已喜极而泣,良久说道:“你种种奇遇简直匪夷所思,不过仅凭你空口白话,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这个好办”,张仨从怀里掏出侍卫腰牌,说道:“楚王府四名侍卫现在住在县城驿站,你派人一问便知。”
张寒山道:“这些人本就是朝廷里的人,我如何相信?”
张仨为之气结,说道:“难不成我去找楚王朱桢,或者南京城里那个朱重八来,让他爷俩给你当面做个见证?”
张寒山摇摇头,向地面跺了跺脚道:“这棵大槐树下,已经埋了三个冒牌货了,这三个狗东西都是冒充我大兄儿子,专程来大环村打探藏银消息的,呵呵,聪明反被聪明误,最后都给这大槐树做了肥料。”
张仨心下一惊,想到自己脚下埋了三个死人,不由向后退了几步。
“你与他们不同”,张寒山道:“大兄的脾气、秉性、喜好无一不晓,这个假不了,好,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想来你父子二人在铁匠庙吃斋念佛十六年之久,来来来,你且背诵《心经》出来,这部佛书短得很,不过二百余字,只要你背得出那就证明你曾是真和尚,我就让你认祖归宗。”
张仨哪里会背诵什么《心经》,不过他反应极快,哈哈一笑道:“要证明我是不是当过和尚,哪里用背经书这么麻烦,你看?”说着伸出头来,一把扯掉头顶的帽子,露出头上不长不短的头发来。
头发不长不短,恰好说明一个事实,几个月前他还是如假包换的光头。在大明朝剃光头的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受了“髡刑”的人,会被强行剃光头发以羞辱本人,另一种就是僧尼了。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也,孝之始也”,所以绝没有人会主动剔去头发。
张寒山伸出颤抖的手,轻轻抚摸着张仨的头顶,泪水慢慢涌出,他信了,彻底信了。
片刻,张寒山大跨步走出祠堂,冲着山下大喊道:“大环村所有男丁听令,一炷香后齐聚祠堂,见证我侄儿认祖归宗。”
张寒山的声音中气十足,尾音在山间久久不绝,霎时间,山坳里沸腾了。
张寒山回过头来,向张仨道:“我只有两女并无子嗣,一会你认祖归宗后,我会宣布你为少族长。”
张仨心中大惊,他可不愿做什么劳什子少族长,随即一脸正色道:“二叔,我刚回村子还寸功未立,且等我立了功劳也好服众,到那时您再宣布岂不是名正言顺?”
张寒山点点头,道:“不争名利,也不冒进,你很好!”
片刻工夫,山下人声鼎沸,亮起一个又一个火把,转眼间火把组成一条长龙开始从山脚下裹向山腰。张仨站在张寒山身后,说道:“二叔,我还有个问题不解。”
张寒山道:“你说。”
张仨看了一眼大槐树,问道:“二叔,方才你说村里我这一辈,名字中都藏有一个‘小’字,咱们大环村这么多人,这个秘密就没传出去?那三个冒牌货就没改名换姓准备准备?”
“传不出去”,张寒山笑道:“全村上下,我这一辈只有我和你爹识字,你这一辈却是无人识字,就连阿香我也没让她识字,呵呵。”
张仨点点头,片刻工夫,嘈杂的脚步声来到祠堂外,领头的正是张宥屁,他向张寒山禀报道:“族长,全村二百三十六名男丁全都到了。”
“好”,张寒山亲手拉着张仨进入祠堂,二百余人也尽数跟进祠堂,将不大的祠堂挤得满满当当,张寒山咳嗽一声,祠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跪下”,张寒山指着排位前一个蒲团喝道。
张仨扑通一声跪在蒲团上,心里那个气呀,暗道老子就是来村里送粮食了个心愿,谁知还真就认祖归宗了,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怪事一桩,这到哪儿说理去?
张寒山在一旁从容地净手洗面,恭恭敬敬取了三炷粗香,在众多牌位前点燃,躬身沉声道:“木本乎根,水本乎源,列祖列宗,听我一言……万盛隆一脉传继千年,时至今日栖身莲花山中,宗族人丁单薄,度日艰难……今日遗珠张仨前来认祖归宗,实乃大幸,全赖祖宗指引保佑……”
张仨在一旁听得昏昏欲睡,却还得跪得笔直,心中暗忖:“废话真多,念来念去也不嫌麻烦,直接让我磕几个头不就了事了嘛?”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过了许久张寒山说完了话,又从数百个牌位最上层开始,一层层一一介绍起祖宗的姓名、生平、功绩等等,真如黄河之水般滔滔不绝。
张仨跪在蒲团上,虽有万般无奈,却还得一五一十认真听着,没办法,几百双眼睛盯着呢!
不过张仨也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最上层祖宗的名字中有什么字,下面排位中若再出现这个字,就会天然少上一划,比如说最高一层祖宗名字中有个“德”字,下面牌位上的“德”字就会缺少“心”上一“横”,再比如说,一个“正”字,张寒山在说第一排牌位上时,这个字念“正”,但下排牌位上再出现这个字时,依然念“正”,但却又少了开头一“横”,成了个“止”字!
“奇怪,奇怪”,张仨心中暗道,难道这刻牌位的匠人是个别字先生?不应该呀,张寒山是认字的呀,岂能让自己祖宗牌位错字百出?
张仨百思不得其解,只听张寒山喝道:“万盛隆子孙张少一,俗名张仨,向列祖列宗叩首进香!”
张仨接过三炷粗香,有样学样点燃了香头,恭恭敬敬插在牌位前的香炉中,又后退几步,恭恭敬敬磕了三个头。
众族人欢呼起来,从这一刻起,张仨就是他们的族人了,张寒山又重重地拍了拍张仨肩膀,朗声道:“你的族名是张少一,将会写入家谱,不过如今你既然已为官,在外仍叫张仨即可。”
张仨又想起大环村“人坏村”的别称,不知怎的,心里似乎划过一道闪电:“少一,少一……人叫少一,牌位上这许多字也能少一“横”,莫不是……”
在他心中,那四句偈语慢慢浮现在脑海中:
“井市烟火晚,
目送瓜州帆。
夫子何所为?
王孙空掌权。”
在他心中,清晰浮现出的这四句偈语是也开始短笔少画,字迹似乎自己游动着少了一笔:
“井”字少一笔成了“艹”,
“目”字少一笔成了“日”,
“夫”字少一笔成了“大”,
“王”字少一笔成了“土”。
当“艹”“日”“大”“土”像积木一般从上到下慢慢摞起来,居然慢慢组合成了一个字——“墓”。张仨心头一阵狂喜:“哈哈,老子真是个天才,怎么以前就没想到呢?那笔藏银原来是藏在陈友谅墓里呀!”
从方长信,到廖家父子,再到当朝皇帝朱元璋,还有那三个不知名的冒牌货,多少人想知道陈友谅藏银的具体地方?张定边至死也没有吐露一星半点。谁也想不到,四句偈语居然被张仨就这么轻而易举地破解出来了。
“哇哈哈……”张仨忘了场合,跪在蒲团上扬起头大笑起来,心里实在得意非凡,一不小心被口水噎住,又打了几个嗝。
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多少年来谁敢在祠堂里又是大笑,又是打嗝?
数百双眼睛疑惑地看着张仨,张仨赶紧止住笑声,向四周团团作揖,解释道:“我父亲从小就嘱咐我一定要重回宗族,我是梦里都想着早日回来呀,如今好梦成真,我……我心里高兴呀!”
众人欢声雷动,都对张仨极为亲热,张宥屁带头,众人乐不可支地冲上来,一次次将张仨高高抛向空中,欢笑声、尖叫声好不热闹……
山里的夜很静,这一夜,张仨睡得极为踏实。
次日日上三竿,张仨被窗外的笑声吵醒,定睛一看,窗户上爬着一溜娃娃脸,笑吟吟地看着自己,领头的正是阿尕。
见张仨醒了,娃娃们喜笑颜开,齐声高叫:“大懒虫,太阳都晒屁股了……嘻嘻!”
张仨一笑起床,阿尕带着几个孩童跑进屋子,又是端水又是叠被对他亲热得不得了。阿尕最是勤快,帮着他叠好被子,伸出手来问道:“仨哥哥,我听姐姐说,你在县城里给小孩发了不少礼物呢,我们干了这么多活,咋没有礼物呢?”
张仨哈哈大笑,摸了摸怀里,索性将七八百斤盐票都递给阿尕,嘱咐他交给各家各户大人去,大人们肯定有赏。
孩子们欢笑着飞跑而去,没过多久,整个村子都沸腾了,这可是七八百斤平价盐票呀,大灾之年有银子也买不到。
阿尕又跑回来,笑嘻嘻地传话说:“阿爹有请。”
张仨随着阿尕来到张寒山家,桌上已经放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张寒山腰系围裙,正在将剥好的白狐皮晾晒起来。
“先吃饭”,张寒山说道:“尝尝红烧狐狸肉,这肉最能补虚暖中。”
张仨却不急着吃饭,近前来看那两张白狐皮,只见绒丰厚平齐细柔,更难得的是一点伤口也没有,不禁啧啧称奇。
阿尕在一旁笑道:“寻不到箭孔的,我阿爹是一箭射中狐狸眼的,哪里会有箭孔。”
张仨笑着抱起阿尕,却见一旁整整齐齐放着一摞盐票,正是他晨起交给村里娃娃的那些盐票。
“来,一起吃饭”,张寒山卸下围裙,招呼张仨上桌吃饭,说道:“这些个盐票价值不菲,按照村里的规矩,盐这精贵东西由族长统一分配,所以大家伙就都交过来了。回头硝好了皮子,你身为少族长跑一趟腿,带着大家伙回县城卖了皮子,正好再买些盐。”
阿尕笑道:“我也要去县城看看,我还没去过县城呢,听说县城里有捏糖人的,那糖人有好看还能吃,比甜菜还甜呢!”
张仨夹起一筷子狐狸肉送到阿尕碗里,问道:“你还没有去过县城?”
阿尕边吃边说道:“不止我没去过县城呀,村里人不到十五岁都不许去县城,这有什么稀奇的。”
张仨抬眼又问张寒山道:“二叔,我爹小时候去过县城吗?”
“十五岁之前,我们兄弟谁都没去过县城”,张寒山说道:“不过过了十五岁,大兄想不去也不行了。”
张仨奇道:“这是为何?”
张寒山说道:“祖训如此,祖训规定‘家贫,长子走险而次子走稳,家富,则长子走稳次子走险。以稳为盾,护家之后方,以险为茅,开前方之路’,所以,大兄十五岁那年,只能出去拼一拼了。”
他放下筷子,心中想起自己兄长张定边,摇了摇头竟有些哽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