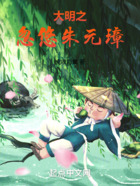
第64章 功名
夕阳西下,满天红霞,禾园也笼罩在一片霞光中,池塘边水波荡漾。
朱桢负手前行,张仨一溜小碎步,跟屁虫一般紧跟在后,嘴里一刻也没闲着:
“王爷,您带来了什么大礼,让我先看看呗?”
“兄弟,我家的包子你不能白吃吧,你说说皇上赏赐我多少真金白银?”
“咋地,说你一句饭桶你还当真呀?男子汉大丈夫就这点胸襟?”
……
张仨在朱桢身后絮絮叨叨一路套话,朱桢却理也不理,刘全虽然和张仨关系不错,但也一脸苦笑不敢搭话。
“先去你这小子的书房看看,再把锦盒给你!”,朱桢终于发话了。
张仨赶紧答一声:“好嘞”,引着朱桢向书房而去,心道去书房就好办,书房是禾园最为安静之处,他估计朱元璋的赏赐不会轻。
张仨自打住进禾园,他就只来过一次书房,说白了,邱成机把这宅子送给他时,书房中檀木书架上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摆了不少,不过张仨看见这些书就头疼,而且他挺迷信,觉得“书”与“输”谐音实在大大不吉利,所以干脆再也不去了。
虽然张仨平日对书房敬而远之,但下人们还是按例每日将书房打扫得一尘不染,各类书目也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
“这些书你都读过?”站在书架前,朱桢并不急着打开锦盒,而是望着琳琅满目的书册问道。
张仨心道:“老子好歹来过一次书房,这些书认得我,我可不认识这些书。”
他抬眼一看,书架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应有尽有,这些他是绝对没有看过的,不过再一看,架边放着厚厚一本《唐诗三百首》,心中大喜,接口说道:“不敢说全读,但还是读过一些的。”
他好歹也是初中毕业,还是背过几首课本上的诗词的。
朱桢点点头,心道这些书没有一千本也有八百本,就是自己从襁褓起,三更灯火五更鸡苦读这么多年,也不敢说全都读过,看来张仨为人还是比较谦逊的。
书房中有一方硕大的茶台,以一方大木树根雕成,树根盘根错节,雕工极具匠心,刘全笑呵呵地主动上前给二位泡茶。
“父皇今日已经动身返回南京”,朱桢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杜少陵集》,说道:“我父皇说,你小子是大才,诗词造诣直追李杜欧苏,皇上说,希望明年南京会试上,能看到你的考卷,这可是你的大造化呀!”
张仨心头大惊,眼睛睁得溜圆,心道:“朱重八这老小子是失心疯了吗?老子八股文章狗屁不懂,诗词歌赋一窍不通,他怎么会觉得我是‘大才’?还直追李杜欧苏。对了,李杜欧苏是什么人,也没听过‘李杜’这个复姓呀?”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李杜欧苏是什么人?可是当朝翰林院大学士?”
朱桢一个趔趄险些没站稳,回身问道:“你……你……不知道李杜欧苏是何人?”
张仨摇了摇头,道:“‘李杜’这复姓少见,想来也不是经常抛头露面的人。”他哪里知道,李杜欧苏是读书人对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的合称。
朱桢面色有些不可置信,和刘全交换了一下眼神,将手中《杜少陵集》翻开,问道:“你可读过这本诗集吗?”
张仨挠挠头,道:“杜少陵是谁?”,他并不知道杜甫自号少陵野老,《杜少陵集》正是杜甫的传世诗集。
朱桢看张仨神色不似作伪,随手翻开一页,强压着心中的疑惑说道:“仨儿,你且读一这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张仨不明所以,拿过书来看了看这首《绝句》心中大喜,这首诗他前世小学时候读过,当下摇头晃脑读起来: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首《绝句》张仨读得抑扬顿挫,好似饱读诗书的老儒一般,他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读完又摇摇头道:“诗是好诗,可惜这印书之人太过马虎,居然印着错别字。”
朱桢凑过脸来,满脸的不可置信。张仨大咧咧地指着书上几处字,说道:“你看,这书上把‘广厦’的广字印成了‘廣’,说起来,‘广’字一看就是茅屋房子的意思,虽然茅屋上的茅草也的确是枯黄色的,但直接把‘黄’字直接印在‘广’下,啧啧,这就画蛇添足了嘛!”
张仨这番高论,直接把朱桢惊得目瞪口呆。要知道,‘广’的繁体字就是‘廣’,张仨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张仨看朱桢目瞪口呆,心中以为朱桢被自己的才学镇住了,又大咧咧说道:“还有这个‘千万间’的‘间’字,好端端两个额角画蛇添足变成了‘間’字,还有这个‘俱欢颜’的‘欢’字,咋就写成了‘歡’字,左半边就一二十个笔画,挤成一个大疙瘩,哪个人写起这个字能心情欢乐?”
朱桢彻底震惊了,这些字哪个不是千年以来就是如此,张仨居然……这只能证明一件事,他看走眼了,眼前的张仨八成是个不学无术之人。不过朱桢心中还抱有最后一丝希望,他难以相信如此粗陋之人怎么又能造出水泥来?这实在说不通呀!
刘全惯会察言观色,见朱桢犹豫不决,放下锦盒替主子出言试探道:“张大人果然博学多才,您这茶台古朴硕大,能否赋诗一首?”
张仨指出了《杜少陵集》中的“错别字”,心中正意气风发,略一思索笑呵呵地说道:“那就献丑了,嗯,‘远看大木头,近看木头大,木头真是大,真是大木头’!”
朱桢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手中的诗集“哗啦”一声掉在地上。
书房窗外不远就是小池塘,阵阵鹅鸣传来,小花狗也汪汪地叫起来。刘全端了一杯热茶递给张仨,张仨心中得意,问道:“刘官家,刚才我那首诗怎么样?古有曹植七步成诗,我一步都没走脱口成诗,是不是也算奇才了?刘管家你可会作诗?”
刘全讪笑了笑,又道:“张大人,我可不会作诗,您听这窗外的鹅叫,我记得有一首诗叫什么‘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诗三岁小孩都会,我比三岁小孩也不如。”
窗外小花狗也叫起来,张仨抿一口茶,此时他诗兴大发笑道:“既然有《咏鹅》,却为何没有《咏狗》?看我现做一首来。”说着,他捻了捻下巴上并不存在的胡须,一字一顿道:“狗、狗、狗,仰头对天吼,喂肉跟你走,打它咬你手。”
“够了!”朱桢一巴掌重重地拍在茶台上,指着张仨大吼道:“他妈的,你……你……你害得我们兄妹好惨呀!”
“兄妹?我怎么坑您和福清公主了?”张仨反问道。看着朱桢脸色铁青,他暗忖难道是昨晚和福清那事儿事发了?也不对呀,朱桢明明说的是“兄妹”,自己可没坑朱桢呀?
朱桢望着满书架的《大学》、《中庸》、《论语》等书籍,回身问张仨道:“你……你老老实实告诉我,这书架上的书,你读过几本?”
张仨看朱桢脸色不对,老老实实地答道:“一本……”
朱桢倒吸一口凉气,心中暗道这小子原来只读过一本呀!却听张仨说道:“一本……也没读过。”
朱桢身形晃了晃,险些没站稳,良久才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你让我可怎么与父皇交代?我可是打了包票的。”
张仨满脸疑惑地问道:“打了什么包票?”
朱桢摆摆手,已经不想再说话了,指了指刘全,让他解释给张仨。
刘全慢慢解释给张仨听,听明白原委,张仨乐得哈哈大笑,险些一屁股坐到地上。
原来,朱桢非常喜欢张仨在沙洲上所作的《临江仙》一词,亲自撰写后装裱挂在书房中,朱元璋偶然看到“滚滚长江东逝水……”后也赞不绝口,很诧异这首大气磅礴的上佳词作竟然出自张仨之手。
蓝玉不知何故,又在一旁大为鼓吹张仨的才华,直把他说成了民间遗珠大才,福清也可着劲儿的拱火,说张仨无偿奉上水泥秘方,皇上却没有论功行赏,硬生生为张仨讨了一个三等侍卫的封赏。
张仨闻言大喜,抢过锦盒打开来,里面果然有一面青布方巾裹着的紫铜腰牌,他当然知道这面腰牌的分量有多重,一把拿起来揣入怀中,冲着朱桢一脸坏笑问道:“还有你送我的大礼呢?不要小气,拿出来。”
朱桢为之气结,看都懒得再看张仨一眼,负手走出书房,临走道:“还有一桩好事,你小子升官了,皇上着你升任两湖观风使,奶奶的,权利大了不少呀,有权写奏章直达天听了!只不过还是无品无极,皇上说等你有了功名再封赏品级不迟。”
“又是无品无极”,张仨一撇嘴道:“还不如这块破头巾呢,还能当个抹布来擦桌子!”
刘全赶紧指着方巾向张仨解释:“张大人,这块方巾还不贵重?大明上下,唯有通过院试的秀才能有资格戴着这‘四方平定巾’,戴上这顶头巾,免除赋税徭役不说,更能身份高人一等,你可不知道呀,王爷为了这顶头巾,担了莫大的干系专门亲自去了一趟府学,硬生生要来这顶方巾,还为你备案了秀才功名。”
“哈,这我就是秀才了?”张仨这才拿起方巾翻来覆去地看看,笑道:“真是小家子气,怎么才是个秀才,好歹给我弄个举人耍耍嘛!”
“兄弟,你错怪王爷了”,刘全拍了拍张仨的肩膀,说道:“两湖秀才七千多人,这些人能见官不跪,免除税赋,但是举人就好处更多了,所以朝廷对乡试慎之又慎,严之又严,无论谁从中徇私舞弊,那都会龙颜震怒,弄不好就是……”
刘权手掌在自己脖子上一切,撇了撇嘴。
朱桢向禾园外快步走去,心头是在恼火,临出宅门时看到刻着“禾园”二字的大石,心中暗道张仨若不读书,怎会给宅子起这么文雅的名字?他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停步询问张仨道:“听闻这‘禾园’的名字是你起的,可是取‘锄禾日当午’之意?”
朱桢心头依然存有一丝侥幸,“禾园”的“禾”自有农为邦本的意思,想来张仨还是有大义在心的。
不料张仨手里摆弄着头巾,大笑道:“什么‘锄禾日当午’?我媳妇肖黎儿的‘黎’字左上角,不就是个‘禾’嘛!”
朱桢一个趔趄,险些被门槛绊倒,心中彻彻底底一凉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