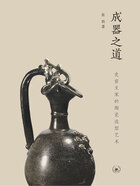
一、史前陶器的器形与纹样
探究陶瓷艺术的发展,不可避免要追溯至史前时期。作为器形与纹饰的起点,原始先民首先考虑到的应该是器物成型的基本理念,即从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出发,结合所在地域的独特自然条件,对器物进行有目的的制造,并使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满足社会活动中的特殊需要。伴随着不同地域之间文化的交往与互动、制造技术的逐步完善,后期不断涌现的器物又在先前的造型与纹饰的基础上进行模仿、融合与创造。
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先民们在最后一个冰期结束后选择了定居生活,采集与狩猎逐步被种植作物与饲养家畜所替代,农业和畜牧业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陶器便在这种历史环境下酝酿产生,成为新石器时代一系列文化遗址中出土最为丰富的人工制品。陶器成型之初样貌如何呢?冯先铭先生曾指出:“黑陶一般盛行于山东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其他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有出土。但已知的最早的黑陶却属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夹炭黑陶……白陶盛行于大汶口文化,各地龙山文化、长江流域大溪文化和各地商文化遗存中亦均有发现。但最早的白陶遗存则出土于浙江罗家角马家浜文化遗址中。”[1]上述现象说明,在史前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类型中,器物的造型与装饰应各具特点,是各群体根据各自的材料和工艺优势而进行的选择。杰西卡·罗森则指出:“早期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即它是几个社会构成的一个复合体。……中国大陆居民的艺术传统的历史并未显示出一个统一的脉络,而是许多不同族群的贡献融合的结果。”[2]信然!
以下从四个方面具体讨论史前时代的陶器问题。
(一)史前陶器纹饰的多种表现
仰韶文化中陶器彩绘常见的题材一类为鱼纹、鸟纹以及蛙纹,另一类是抽象的人面与鱼纹形成的组合图案,一般出现在盆的内壁上,最著名的例子当属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图1)。马家窑文化在文化特征与艺术风格上是仰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鸟纹开始几何化,大量较具象的蛙纹图像覆盖在盆或钵的内壁,随后也开始简化,人形纹饰也出现在马家窑彩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图2)。龙山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史前文化之一(图3),其发现给我们认识陶器的纹饰功能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山西陶寺的陶寺龙山文化遗址早期大墓中发现的蟠龙纹陶盘……蟠龙纹是在陶盘低温烧制后绘上的,因此它们不可能是实用器,而且在一座大墓中只随葬一件蟠龙纹陶盘。陶寺遗址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发掘者认为陶盘是祭器,蟠龙是氏族、部落的标志。……陶寺龙山文化时期的彩陶上还流行绘饰云雷纹图案,这种时尚也见于其房屋建筑上的装饰遗迹,诸如在墙面的白灰面上刻饰有类似商周青铜器装饰的几何形图案”[3]。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年代在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间,器物上的纹饰常见的有太阳图案的动物纹饰,陶器也是如此,例如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猪纹陶钵(图4)。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反山遗址出土的属于良渚文化的玉钺,学者注意到刻在刃部附近的人面与兽面组合图案可能不仅是装饰。作为礼器的钺彰显着其所有者的权力,而人面、兽面相结合的纹饰在礼器上出现,除了装饰作用外,更为突出的应是作为某种标志,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类人面、兽面纹还出现在一些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在陶器上也出现了,江苏苏州澄湖出土的兽面纹和鸟纹黑陶罐上就刻画了更为具象的此类形象。

图1:人面鱼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高16.6厘米、口径39.8厘米,陕西省西安市半坡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舞蹈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高14.1厘米、口径28厘米,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红陶鬶,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高39厘米、口径12厘米、足距14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4:猪纹陶钵,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高11.7厘米、宽17.2厘米、长21.2厘米,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在史前时代出土的大量陶器中,以上所提到的采用图绘和雕刻手法、装饰别有意义的纹样的实属少数。在现今出土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龙山文化、河姆渡文化以及良渚文化的陶器中,更多器皿的装饰手法是素面磨光,采用几何装饰纹、拍印的绳纹、篮纹、附加堆纹、划纹及弦纹等。可以推测,制作者在对陶器进行纹样装饰时是有所选择的。不同的装饰手法,一方面是来自对其他制作工艺的模仿,如绳纹与篮纹的大量流行即是如此。早期陶器既在造型上模仿篮子、皮袋等已有器物的形状,同时也从篮筐编织成器的方法上获得启发。先民们采用泥条盘筑的方法由下至上合成全器,再用陶拍拍打其表面。若陶拍上刻有花纹,便形成了可见的印纹。另一方面,陶器上的装饰纹样又与原始陶器制作者的感官知觉有关,“这种设计是与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受居住条件的限制,他们席地而坐或者蹲踞,所以彩陶花纹的部位,都是分布在人们视线最容易接触到的地方”[4]。而在这些原始的本能和模仿之外,另一部分别有意义的装饰图案的形成与功能倾向,下文将结合陶器器形做进一步讨论。
(二)史前陶器器形的多种功能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主要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实用器,因此根据功能可以分为罐、鼎、鬲、釜、甑、鬶等汲水器和炊器,爵、角、觚、杯等饮器,碗、豆、簋、盘等食器,壶、罐、瓮、尊、盆、缸等盛贮器。这些器物各具特征的形制与其使用功能密切相关。
器形的多样化也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1)在社会分工上,逐渐由家族集体制陶、季节性陶工,向专门从事制陶工艺的人员发展;(2)陶窑结构的逐步完善使得烧制条件趋于稳定,并为铜器的制作提供了设备参考;(3)烧成温度的可控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4)不同文化区域对陶器制作的成形方法与纹饰有不同倾向的选择;(5)出现陶料的精选以及制陶原料的多样化。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一件器物可能承担了多种功能,或者说存在器形通用的情况。如早期仰韶文化遗址与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一些陶器,在器壁上绘制或刻画了特殊图案的同时仍然具有实际用途;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则出现了一些器皿,它们在成器的制作手法上似乎有意偏离之前所掌握的能满足实用功能要求的技术与经验,转而去突出不合逻辑的结构形式与非实用目的的外观美感。
大汶口文化位于黄河流域下游的山东与苏北一带,那时先民们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制陶技术,手工泥条盘筑法之外,轮制技术也已经发展成熟,除灰陶、黑陶外,还出现了用高岭土制作而成的白陶。该地区出土的鬶便多是用白陶制作。鬶通常是锥状三足,足部为球状或袋状,中空,这有利于加热液体;三足相交于一个带口沿的圆颈,口沿外翻方便倾倒;在足与器颈之间装有一个手柄,用于提起器皿。1977年,山东省临沂市大范庄出土了一件属大汶口文化的双层口白陶鬶(图5)。这件陶鬶三足尖细修长,颈部呈高直状,口部有帽状装饰,器壁很薄,手柄制作成单薄的长片状安于其上。如此深的垂直容积、不具提举功能的手柄,以及薄巧的器壁之间,出现了成器的逻辑矛盾。这种偏离实际使用功能,突出器皿整体空灵精细的造型追求,在后来的龙山文化中呈现得更为明显。一种被称为蛋壳黑陶杯的器皿(图6),它也有着纤细高挑的杯柄,薄如蛋壳的杯体——如此惊人的薄度需要杯体由没有杂质的细腻黏土制成,以及通过高超技术打磨光滑的黑色器壁。重量仅有50至70克,杯体与支架有轮制的痕迹,有些杯体与支架还可拆分。蛋壳黑陶杯的出现,表明陶器的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纯熟,制作者与使用者却没有将其用于制作更符合实际功用的器皿,而是将巨大的人力、物力凝聚于将一件陶器特殊化。这表明,在生产力逐步提升的同时,社会也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

图5:双层口白陶鬶,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高36.8厘米,山东省临沂市大范庄出土,临沂市博物馆藏

图6:蛋壳黑陶高柄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高22.6厘米,山东省潍坊市姚官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三)原始陶器与墓葬等级制度
考察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城北公元前5000年至前4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属于仰韶文化的姜寨遗址,壕沟内100多间房屋被分为几组,每组拥有一个公共集会用的“家族房屋”。在遗址西南的临河岸有4座窑址,这表明陶器制作已经有较高的产量和质量,并且可能是以集体劳动的方式进行烧制的[5](图7)。该处出土的陶器都具有日常用器的特点,在遗址的发掘中没有发现随葬品奢华的墓葬,说明当时并未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

图7:姜寨遗址示意图
而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形制之间的差异则显示出村落中的某些居民比其他人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社会财富。1959年发掘的位于山东省泰安市的大汶口遗址,其大型墓地可分为3个连续时期,包括133座墓葬。位于墓地北边一组12座墓葬中的10号墓可定为晚期,为这批墓葬之冠。相比其他中小型墓,该墓的长方形墓穴达到12平方米。墓主人经鉴定是一位50至55岁的女性,她在出土时佩戴有三串石质装饰品。葬具外放置着大量的陶器,有白陶、黑陶、彩陶等,均十分精美,这其中以白陶所处的位置和数量较引人注意。该墓同时还出土了石斧头和雕琢的象牙管。这些随葬品显示了墓主人生前拥有的可观财富[6](图8)。理查德·皮尔森(Richard Pearson)对东部沿海的一批随葬品甚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做了全面分析,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沿海属于大汶口文化序列的新石器时期墓葬反映了财富的增长,社会的分化和妇女儿童地位的下降……它正在向一个由男子掌握权力和财富,手工业分工即将发生的社会转化。某些特殊的男女和小孩合葬墓,表明宗族的重要性在增加。”[7]

图8:大汶口遗址墓葬出土发掘情况
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父系氏族的权力特征更加凸显出来。资料表明,两个龙山文化村落里有了夯土墙,定居模式已经超过了仰韶文化的村落社会阶段。河北省邯郸市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袭击村落的迹象,有扔在井里的遗骸,可能被剥了头皮的头骨,这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有了战争[8]。山东省潍坊市呈子村附近龙山文化遗址中的墓葬里发现的蛋壳黑陶杯,随其他陶器如鬶一起作为陪葬品,但仅有6%的墓葬拥有这些精美的陶器(图9、10)。拥有陶杯的墓葬陪葬品都较为丰富,墓穴都较大,并且有木椁痕迹。蛋壳黑陶杯被放置在死者的头、胸部、手附近[9],可能表明死者具有特殊地位,或是作为统治阶层。由此可见,早期的季节性陶工和集体制作的活动已经逐渐减少,蛋壳黑陶杯由技术熟练的全职陶工耗费大量工时进行限量制作,用以满足地位较高、权力较大的使用者的需要。且葬礼可能具有相关仪式,制作精良的蛋壳黑陶杯就此作为具有特殊功用的器皿,被安排在葬礼的使用中。

图9:黑陶双系壶,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高11.5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8.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图10:黑陶高柄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高15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6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四)史前陶器的纹饰与器形的启发
通过考察史前陶器的器形与纹饰便能发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聚集与权力意识的形成,陶器发展呈现出多条线索。
就实用功能而言,早期陶器具有器形通用的情况,而技术的成熟使得器形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形成相对固定的样式,并在此过程中淘汰一部分器形,随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中出现了不出于实用目的而制作的器皿。至此,陶器在功能上形成实用器与“特殊”器皿的两分。
此类情况也反映在纹饰上,“史前器物上的某些图像与符号兼有装饰和标志两种功能,有些标志具有青铜器图形文字的作用。身兼两职的现象在史前晚期文化中甚为普遍”[10]。现在学界对各文化区域的陶器纹饰上反复出现的题材已有诸多讨论,观点分别有图腾崇拜、萨满巫术、太阳崇拜、生殖崇拜等。虽然这些推想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都反映出陶器的装饰图案所具有的两种倾向:一是对前期技术与审美经验的继承与复制;二是在含义上对宗教信仰与种族特征进行有目的的反映。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由初创阶段发展至青铜时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信仰与宗族特征便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对技术经验与审美倾向的继承与复制反映出,在史前时期各文化区域间就可能已出现相互交流影响的情况。
在一类非实用目的的陶器制作上耗费大量的人力,特殊纹饰的出现,采取精选的原料,所有这些均表明夏商周时期“礼”的特殊概念在史前时期的陶器上出现了萌芽。当世袭的王朝模式与礼制样式在中原确立,“戎”与“祀”成为支持与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活动,并在整个古代中国范围内被更广泛地接受,礼器与用器便有了更为明确的区分。张光直先生指出,政治权威在夏商周时期逐渐形成的过程中包括:(1)个人在一个按层序构成的父系氏族和分支宗族的亲族体系中所占据的地位;(2)相互作用的区域性国家网络,每个国家都控制着重要资源,它们共同形成连锁的、互相加强的系统;(3)军事装备,包括青铜武器和战车;(4)有德之行为(为大众谋利益的品质),它为在位的统治者依神话权力所继承并身体力行之;(5)作为信息载体的文字,它与个人在亲族体系中的地位有关,与神灵(祖先)的知识有关,是取得统治和预言能力的关键;(6)通过文字以外的手段,如巫术仪式(及其乐舞)以及动物艺术和青铜礼器,以达到独占与在天神灵沟通的目的;(7)财富和它的荣耀。[11]
显然,物质上的易碎性与展示财富上的低廉特征都是陶器作为“礼制”承载物的缺陷,于是对原料的精选行为随后转化为用新出现的贵重且耐久的金属材料替代陶土,在陶器与玉器上出现过的特殊图案则被金属材料更进一步地强调而趋于象征化,“从材料到外形,再到装饰与铭文,这一系列演进中的变化焦点展现出礼仪美术特征的变化,即从最实在到最抽象,从自然因素到人工的标记”[12]。青铜时代的礼器对已有的陶器样式进行模仿与创新的过程同时也是武力征伐与政治权力更替的过程,不同物质文化背景下族群间的共存、迁徙与交流,反过来也影响到了陶器器形与纹样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