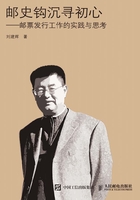
02 邮票发行工作的“兰德”现象——记邮电部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的创立
什么是兰德?什么是兰德现象?
兰德,是美国一家智库的名称。它是美国最重要的以军事为主的综合性战略研究机构。它先以研究军事尖端科学技术和重大军事战略著称于世,继而又扩展到内政外交各方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被誉为美国现代智囊的“大脑集中营”“超级军事学院”,以及世界智囊团的开创者和代言人。它可以说是当今美国乃至世界最负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长久以来,兰德公司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事务的决策。在为美国政府及军队提供决策服务的同时,兰德公司利用它旗下大批世界级的智囊人物,为商业企业界提供广泛的决策咨询服务,并以“企业诊断”的准确性、权威性而享誉全球。说穿了,兰德公司就是美国政府的“外脑”。那么,兰德公司和邮票发行工作有什么关系呢?这还要从30年前的一段往事谈起。
1985年,邮电部对中国邮票管理体制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将中国邮票总公司原有的职能一分为二,即邮票发行管理部门和邮票经营部门分开,组建邮电部邮票发行局和中国集邮总公司。这是改革开放以后,邮电部对政企合一的中国邮票总公司第一次做出带有政企分开性质的重大调整。新组建的邮电部邮票发行局为正局级单位,主要负责邮票发行等政府职能。中国集邮总公司为邮电部直属正局级企业,主要负责集邮业务经营工作。邮电部在这次改革中,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决定,做出了一个在当时堪称破天荒的决定,就在邮票发行局的领导职数中,增加了一名专业领导干部。1985年7月3日,邮电部部长杨泰芳签署了(1985)部任字31号,任命邵柏林为邮票发行局总设计师。

邵柏林,一个对邮票事业的热爱几近痴迷的人,坐不住了。他知道,刚刚改组成立的邮电部领导集体,都是邮电部门出类拔萃的年轻知识分子。要改变邮电通信的面貌,非他们莫属!历史机缘可能稍纵即逝,于是邵柏林秉笔直书,他要把憋在肚子里多年的话痛快淋漓地向部领导报告!
很快,邵柏林亲自撰写的《关于提高我国邮票设计质量的报告》,送到了邮电部杨泰芳部长和主管邮政工作的朱高峰副部长的办公室。他在报告中向邮电部提出了两项改革措施:一、敞开大门,邀请社会美术家和平面设计方面的精英参与邮票设计。建议邮票图稿由专职人员设计的同时,向社会美术家广泛约稿、征稿,使全国千百万美术家也有机会参加邮票设计工作。使一个题材多几人设计,多几个方案,从中择优选用。这样既发挥了专职设计人员的积极性,又调动了广大社会美术家的积极性。我们既邀请著名的美术家参加邮票设计工作,又注意发现名不见经传、富有才华的青年人,让他们有机会一试身手。二、组成以著名美术家为主的,包括集邮家、出版家、专业设计人员和邮电部、邮票发行局的行政领导参加的评审委员会,对邮票图稿的思想性、艺术性把关,这项措施的实质是实行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尊重内行的意见,按艺术规律办事,以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邮电部部长杨泰芳在听取邮票发行局汇报时,充分肯定了邵柏林提出的两项改革措施,指出:邮票评审委员会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好比是我们的外脑,我们的“兰德公司”,我们要尊重专家的意见。
这是邮电部杨泰芳部长对成立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这样一个非常设机构的充分认可,并将设立邮票评审委员会的作用比作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啊!
邵柏林提出的这两项改革措施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尽快提高我国的邮票设计质量,第一步先达到国内最好水准,第二步再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这条路走得通吗?对改革触及的阻力有充分的准备吗?邵柏林没有瞻前顾后,而是像一个战士,既然冲锋号已吹响,就必须一往无前向目标冲锋!
我曾经问过邵柏林,你的前面充满荆棘,为什么还要义无反顾?邵柏林拿出一份保存完好的资料。这是中国邮票总公司多年前的一份内部简报,名为《集邮动态》。在第十四期上刊登了一篇群众来信。但这封来信的作者身份有些特殊,他是当时澳门的集邮者苏兆雄先生。他在给邮电部领导撰写的这份长达近7000字的亲笔信中,对国内的邮票设计质量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邮电部领导将这封信批转到中国邮票总公司。总公司领导把这封信在《集邮动态》全文发表。中国邮票总公司在这篇来信前加了编者按:
“澳门苏兆雄先生最近给邮电部寄了一封长信,谈他对我邮票的意见和建议,语意恳切,批评尖锐,对我们改进邮票工作很有帮助,特转载于此,供作参考。”
苏兆雄先生的来信比较长,为了让读者大致了解这封信的主要内容,笔者特摘录其中部分如下:
邮票的画面设计
邮票的画面设计是邮票制作的首要部分。我国不乏优秀的美术工作人才,为什么不少邮票的画面设计水平却如此低劣?
1.用色 我国邮票的色调不够和谐,用色过分鲜明,尤其红色用得太滥。请多参考英、美、德的邮票用色。
2.技法 有些邮票画面绘制得不够成熟。像T39“五业兴旺”,T75“公众服务中的妇女”,人物呆滞。还有些群众看似木偶,缺乏生气。
3.构图 构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画面的优美。像T38“长城”的构图缺乏雄伟的气势,尤其第4枚不知所谓。中国邮票在处理人物位置布局方面,很多时候都喜欢用排列的方式,就像人物排成小合唱一般,又像摄影全家福一般,缺乏生动活泼。
4.风格 我们当然要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近年来极少看到像T15“首都名胜”那样精彩的雕刻版邮票。不知是什么缘故?
5.套金套银 中国邮票常见套金套银,这种处理,间可为之就好了,不可太滥。
6.主题表现 邮票无疑是宣传的有力工具之一。正因为如此,邮票既要突出主题,又须力避做作。在我们国家突出政治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必须避免教条式地来突出政治。
7.小型张 在小型张中,“长城”那枚最差,底色灰暗,构图零乱。我不明白为什么选这张小型张加印金字来作纪念里乔内第31届国际邮票博览会?但这枚小型张也说明了中国邮票制作水平的低劣。总之,小型张必须有其特色。如果像“全国科学大会”那样的小型张,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苏兆雄先生最后质问“我们优秀的美术工作者都到哪里去了!”
这封信我没有全部照搬,一是文字过长;二是举例过多,涉及太多的邮票设计者。我不想让我的朋友难堪。我相信,苏兆雄先生不是对我们的邮票设计家有成见而措辞尖锐,而是对我国邮票设计的水平痛心疾首,直抒意见,同时也对邮票发行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
这封信对邵柏林等邮票设计者的心头不啻是狠狠一戳!邵柏林把这期简报看做长鸣的警钟而珍藏起来,他不相信中国邮票的设计永远停留在这个水平上。他认定,只要中国的优秀艺术家参与进来,中国邮票走向世界指日可待!
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里的专家请谁好呢?作为上世纪50年代初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学生,邵柏林对学校的老师实在太熟悉了,那是一批中国顶尖的艺术家啊,吴作人、李可染、张仃、黄永玉、周令钊等老师,经过历次风雨走出来的这些艺术家,在老百姓看来,个个如雷贯耳。其实,邵柏林的心里已经有了评审委员会的初步名单。但是,他还是想听听老师的意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是他第一个拜访的老师。随后,邵柏林又去拜访了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华君武先生。两人推荐的名单出奇的一致。黄永玉、周令钊、伍必端、邱陵、郁风,再加上张仃先生、华君武先生,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的基本架构就成型了。这些大艺术家在粉碎“四人帮”后都像换了个人,个个精力充沛投入创作,犹如迎来了第二个创作的春天。他们都肯牺牲自己的创作时间,来参加邮票图稿的评审吗?邵柏林决定亲自登门一家一家拜访。众位艺术家听到“为了尽快提高我国邮票的设计水平”这样一项重任,纷纷举手赞成。原本让邵柏林很纠结的落实工作,居然迎刃而解了!
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主任委员:赵永源(邮票发行局局长)
副主任委员:华君武、张仃、黄永玉
委员:刘天瑞(邮政总局局长)、周令钊、郁风、伍必端、邱陵、邵柏林、王仿子、成志伟、林丰年、董纯琦、李印清
秘书长:邵柏林(兼)
从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成员构成来看,我国著名美术家7人,出版印刷专家1人,集邮家2人,专业人员2人,邮电部和邮票发行局有关领导3人,共15人。
其中成志伟是中宣部的干部,也是集邮界代表,另一位集邮界代表为林丰年。王仿子是出版印刷界专家。
1985年10月15日,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正式成立。邮电部副部长朱高峰和邮票发行局党委书记许宇唐、局长赵永源出席成立大会。朱高峰向每一位评委颁发了盖有国徽图案的邮电部大印的评委证书,并代表邮电部对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在谈到邮电部成立评审委员会的目的时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邮票的发行数量有了很大的发展。邮票图稿设计上也出现了一些受群众喜爱的邮票,有了一支专业设计队伍。但是随着人们对邮票需求的不断提高,在邮票设计和印刷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也不断收到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由于邮票流传很广,一枚邮票设计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文化艺术水平的高低,因此,为迅速提高我国邮票设计质量,我们一方面采取专业设计与向社会约稿、征稿相结合的方式组织邮票图稿创作;另一方面邀请各方专家组成评委会,加强对图稿的评审工作,择优选用,以期尽快提高我国邮票设计、印刷质量。这就是我们成立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的目的。”
秘书长邵柏林宣读了评委会工作规则。主要是,为把我国邮票艺术质量迅速提高上去:一、搞事业,不搞山头;搞科学,不搞关系学;搞艺术,不搞权术;二、为了保证邮票图稿评审的公开、公平、公正,参加评审的邮票图稿一律不署名,只标注第一方案、第二方案等;三、邮票图稿的作者严禁私自找评委说情,一经发现,立即取消邮票图稿参评资格。

这些规则成为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评审邮票图稿时每个人必须遵守的纪律,也使每幅邮票图稿都得到公开、公平、公正评审的保证。那么,这些大艺术家如果参加邮票图稿的竞争,是不是有特例?亦或是否得到特别关照呢?邵柏林讲了在评审邮票图稿时的一桩往事。评委周令钊先生是我国著名美术家,第一轮生肖狗票就是周老担纲设计的。他也曾参与了一套邮票图稿的创作,并送来图稿参评。由于送评的邮票图稿都不记名,在认图不认人的情况下,另一套邮票图稿被评委选定,周令钊先生的图稿落选。事后,评委们才知道谜底。这件事成为各位评委印象极其深刻的一桩往事。
当时邮电部的这两项改革措施究竟执行得怎么样?效果如何?我国1986年、1987年邮票设计水平有没有提高?有没有对这两年邮票设计水平的总体评价?










我在翻阅1987年出版的《人民日报》时,发现了这样一篇报道。1987年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
我7种邮票被日本评为世界杰出邮票
据日本《邮趣》杂志1986年12期报道,我国1986年发行的《木兰》邮票被评为世界25套杰出邮票之一,这是去年我国发行的邮票被该杂志评出的世界第7套世界杰出邮票。被评为世界杰出邮票的中国其他6套邮票是:《民居》《哈雷彗星回归》《白鹤》《国际和平年》《十二生肖虎年》(应为《丙寅年》)和《航天》。
看了这则报道,让人大跌眼镜。日本这个国家,一向自视甚高。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根本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现在居然对中国发行的邮票大加赞赏,岂不怪哉?细想一下,也不奇怪。对各国发行的优秀邮票或称杰出邮票,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东方国家,尽管民族不同、观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对艺术的美丑妍媸的赏识却是相通的。特别是《邮趣》的评选完全出自民间,出自民意的自由选择。因此,对美的事物的标准,对艺术的理解,是可以有共识的。

在日本评出的中国7套世界杰出邮票中,有一套值得一提。这就是《1985-1986哈雷彗星回归》。这套邮票的作者是当时还就读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袁加。30年后,还是这个袁加参与了《长江》和《黄河》特种邮票的设计,这两套邮票都被评为当年的“最佳邮票”。还有一套设计水平与《哈雷彗星回归》比肩的,就是1986年9月10日发行的《教师节》纪念邮票。设计者也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当时在读的学生张磊。他们的设计天赋在学校已经初露锋芒。被称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高材生“三杰”的还有一位,就是王虎鸣。可惜的是,“三杰”中的两杰,后来被留校任教,没能和王虎鸣一起从事专职邮票设计工作。
在日本《邮趣》1987年评出的25套世界杰出邮票中,中国又有10套中选。对此,《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给出了答案。这篇题为“我国邮票艺术质量显著提高的原因是——邮票设计向整个美术界敞开大门”的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
“邮票被称为‘国家的名片’,过去邮电部的邮票设计,基本上由专业设计人员负责,常常一个题材一个人画,没有选择的余地,形成一种封闭的、缺乏竞争的局面。
1985年下半年,邮电部确定了两条改革措施。两年过去了,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文章借用了几位美术界的人士,进行了评说: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美兰指出,近期我国邮票从总体上说发生了值得注意的转向:设计观念由封闭转向开放;审美意趣由单薄转向厚重,由平庸转向高格调;由小景观转向大国风范。这种发展趋势是可喜的。《中国古代体育》借鉴了汉画像砖,以古拙之美诱人;《珍稀濒危木兰科植物》则典雅、大方;《辛亥革命》有时代风云的悲壮氛围,人物与背景的关系处理得相当出色;《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则刻画出一个泱泱大国领袖的风度。邮票艺术是美育的神奇通道,人民需要开拓性的多样化的设计风格。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刘巨德说,发动全国的画家来设计邮票有利于多种艺术风格并存。实践证明现在风格是多样的。我们需要写实的东西,也需要写意的、象征的、抽象的、变形的东西。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袁运甫说,邮票艺术不能完全用“大众化”的语言,还应当有思想性和艺术性。采取广泛招标、集思广益的办法是很好的。
著名美术家张仃教授说,我参加过几次邮票图稿评审会,可以说是严肃认真的,始终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评的结果也是令人满意的,对太差的稿子就行使否决权。我认为这样坚持下去,中国邮票艺术水平的提高是大有希望的。
1986年最佳邮票






1987年最佳邮票






1988年最佳邮票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两项改革措施的实施,我国邮票的设计质量得到明显的提高,形成了新中国邮票设计的又一个高峰。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这个邮票发行工作中的兰德现象,也一直延续至今。
我衷心希望,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这一提高邮票设计质量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坚持数年,必有好处。
在这篇文章已经画上句号的时候,我不得不对一件以讹传讹的说法进行澄清。我国邮政部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究竟有没有“邮票审核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或是临时机构?经向邵柏林、孙少颖等老先生求证,均言辞凿凿地回答:从没有这样一个机构。
注: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从第二届开始名称改为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1998年国家邮政局成立后,新组建的这一机构,也沿袭了这一称谓:邮票图稿评议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