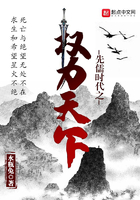
第13章 群英华宴
太康六年,贾充、刘毅、杜预等老臣相继过世,武帝司马炎的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他开始像历代君王一样,寻觅起长生不老之方。
这日,司马炎单独召见汝南王。
“朕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了……”
“陛下只是小疾,陛下一定会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司马炎摇摇头说道:“从始皇帝起,谁不想万寿无疆?朕的身体,朕自己清楚。今日诏你来是有两件要事相托,第一件事,是关于皇太孙司马司马遹的生母谢玖,一旦朕不能临朝,朕会派内侍张让诏你进宫,到时候你就带她离开洛阳,永远不要回来!绝不能让她落在任何人手上,你明白吗?”
司马亮面露难色试探着问道:“倘若不能保时,能否杀之?”
司马炎闭眼沉思片刻后说道:“毕竟是其生母,尽量留她一命吧!以待日后司马遹继位吧!”
“臣明白,陛下所托之事,臣万死不辞!
司马炎从床边拿出一块金牌递给司马亮。
“有了这道金牌,你可随意出入皇宫,也可临时调动皇宫的禁军。”
司马亮恭敬地接过那道金牌。
司马炎点点头继续说道:“还有一件事,你还记得那个南华仙人吗?你还能找到他吗?”
“恐怕找不到了。”
“你说他真的是从汉末活到了现在吗?那他有多少岁?”
“如果是真的,他起码有一百四十多岁了。”
“他有没有长生不老的药方呢?哪怕只是延年益寿的方子!他既然号称仙人,又活了这么久,必定有什么仙术灵丹!朕想见见他,你去把他找来!”
“可是见过他的人少之又少啊!就连臣也快记不清他的模样了。”
司马炎闭目凝神良久,说道:“那个秦婴,还活着吧!朕记得他说见过南华仙人,那就让他去找!去找南华仙人!”
冬去春来,太康七年(公元286年)春分这一日,惠风和畅,洛阳城内大批名士齐聚铜铃大街汝南王司马亮的府邸,可谓群贤毕至,满庭风雅。这乃是武帝交给司马亮的一个任务,因为有大批南方名士北上做官,在洛阳自成一派,北方名士看不起他们,再加上文化差异,所以南北名士之间难免会有冲突和矛盾,为了让南北文化相融,同时进一步笼络南方名士,进而稳固政权,武帝特命司马亮每逢佳节,宴请南北群贤,加深交流,增信释疑。
参加宴会的的不仅有朝廷重臣,更有南北门阀士族,中间座次由东向西依次为杨骏、司马亮、卫瓘三人,东边以颖川荀勖为首坐的都是北方士族,西面以江东陆机为首坐的皆为南方名门,座次由南向北依次为三公、大家士族代表,及各级官员。除了颖川荀氏和江东陆氏之外,还有河东裴氏、清河崔氏、弘农杨氏、平阳贾氏、泰山羊氏、东阳陈氏、琅琊王氏、安定胡氏,此外还有山涛、左思、嵇绍、陆云、周处等名士,齐王司马囧及皇太孙司马遹因与汝南王之子司马瑾交好,也应邀而来。其会不可谓不盛。
国丈杨骏因女儿为杨皇后备受恩宠,其势力越来越大,甚至超过了汝南王司马亮。酒乐正酣时,国丈杨骏乘着酒兴说道:“今日天下名士齐聚汝南王府,名士中有南方人,也有北方人,有人说论打仗,南方人不如北方人,论文采北方人不如南方人,果真如此吗?不如比较比较,助助雅兴如何?”
宴会上的官员名士皆知杨骏近来得宠,所以杨骏的提议,众人无不点头称好。
太保卫瓘长眉狭眼,虽年近古稀,却显得十分精神。他不同意杨骏的意见,用手捻着下巴上的短须说道:“如今天下一统,四海升平,不应再有纷争,大家不论南方北方,都是晋臣。”
杨骏本想看个热闹,不想被太保卫瓘阻拦,若是别人,杨骏根本不放在眼里,但是这个卫瓘,曾参与平定过邓艾、钟会之乱,深受武帝器重,能文能武,且是皇亲国戚,曾官至司空,后逊位,现拜太保,虽无实权,但是说的话还是颇有份量,杨骏也不得不有所忌惮。
“卫公说的极是,我的意见也只是为了交流而已。”
杨骏是个城府小人,自觉失了面子,脸上堆笑装着不在意,心里却深恨卫瓘。刚刚那些依附杨骏点头称好的人,听了卫瓘和杨骏的话,一个个见风使舵,以卫瓘的话为是。
此时却闻听席间有一人高声说道:“我赞成杨国丈之论!”
众人循声望去,只见远处宴席的最末端,一个身穿灰色袍衫的人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杨骏故意装作没听清,命其近前答话。
只见那人行至杨骏等人面前,拱手说道:“在下赞成杨国仗之言论,正因当今四海升平,才更应该在此盛会上比试一番,国丈之意,文章需要交流才能进步,武艺需要切磋才能提高,《左传》曰:‘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天下统一不能贪图安逸,南北差异不该遮掩饰非。只有在盛会之上,交流比试,才能增信释疑!”
杨骏听得这番话,不仅满意,甚至得意起来。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那个谁,你叫什么名字?”
“在下名叫张乌。”
“张乌?现任何官职?”
“无官职。”
“我见你口才不错,你可愿意做我的幕僚?”
张乌叩首道:“张乌愿意,谢国丈!”
“好,你且坐在我的幕僚之首吧!”
张乌凭借自己逢迎拍马之能,一下子从宴会的下等席跻身为上等席的宾客,并坐在了杨骏幕僚的首席位置。
卫瓘还想反驳,但见杨骏当场赞誉这个张乌,自己再驳斥他,就有点太不给杨骏面子了。且自己身份高贵,与一个无名之辈锱铢必较,也难免会被人笑话,故而卫瓘也不再说什么了。
汝南王司马亮担心南北名士矛盾被激化,于是说道:“既分南北,差异肯定是有的,虽为比试,还是要有所限定,主要以交流为目的啊!”
杨骏本就想压汝南王一头,于是故意说道:“交流也好,比试也好,总要分出高下以助兴!魏主曹丕说‘文人相轻’,今天有这么多文人在这里那就比试比试,看看曹丕说的对不对,汝南王,你说呢?”
汝南王不愿得罪杨骏,觉得交流比试一下没有什么关系,于是答应道:“既然国丈一再提议,南北名士交流一下也好,只是不可太认真,免伤和气!”
杨骏见汝南王同意了,满意地说道:“助兴而已,怎么会伤和气呢?不知哪位名士愿意先来?”
时东吴已故丞相张悌之子张勇在座,闻杨骏之言,立马起身,也不施礼,高声问道:“好是好,只是不知比点什么?”
其声高亮,不卑不亢。
杨骏见其无礼,轻蔑一笑道:“原来是原东吴丞相之子!这样吧,晋国既然是用武力夺得天下,我看就不用比武了,也怕伤了和气,不如文斗吧!”
张勇道:“既然是南北比试,文武都应该比一比,我且先上场舞剑给在座诸位添分雅兴!”张勇一边说,一边走上了高台,“不知哪位北方将军敢来应战?”
所有人都知道,谁若能在今日此等宴会崭露头角,必定会名声大噪,之后定会受到权贵们的举荐而飞黄腾达。
席中果然有那北方的年轻小将杨林,属于是杨氏一族,官职为七品牙门将,初生牛犊,没怕过人,见张勇年轻瘦弱,口出狂言,又见许多名门权贵在座,想趁机扬名洛阳,于是应战道:“久闻张勇将军之名,我杨林很想和‘丞相之子’比试比试!”
那张勇虽为原东吴丞相张悌之子,却自小生活于军旅之间,英勇无畏,虽看似瘦弱,却十分有力,其父张悌曾与晋军决战于板桥,死于晋人之手,当时张勇年少,未能随父征战沙场,故张勇心中一直有怨怒。那杨林虽然练过拳脚,但是其陪练者皆趋炎附势之辈,不敢真的打他,所以这杨林其实根本没有实战过,心态上却傲慢地以为自己武艺颇高。
二人赤膊上场,杨林一脸轻视,毫不把那张勇放在眼里,刚一上来就直奔张勇命门而去,不料其招式却被张勇轻松化解,杨林一时恼怒,步步紧逼,张勇隐忍不发,招招化解。数招以后,那杨林已是气喘吁吁黔驴技穷,张勇却是从容不迫还有余力。旁人看得清楚,那张勇分明就是在戏耍杨林。杨林也终于感受到二人在武艺上的差距,胳膊也颤抖起来。杨勇见状,心中冷笑着上前一步,一拳打向杨林胸口,面对这一直拳,杨林似乎忘记了躲闪,愤怒与恐惧令他四肢变得僵硬,他下意识地架起双臂来挡,但他想不到,这一拳竟将他打飞十步远。
南方名士本来听杨林狂言无礼,多有不满,此时见那杨林被打倒在地上,纷纷叫好,北人顿觉得丢了几分颜面,心生怨气。
杨林趴在地上承受着众人鄙视的目光,他本想通过这一战扬名洛阳,没想到却是贻笑大方!此时的杨林已无法冷静,他从未受此大辱,他已经气得浑身颤抖失去了理智,怒吼着爬起身与张勇再战。他疯狂地一拳拳打向张勇,已然没有了章法,张勇挺起胸膛任他的拳头打在自己身上,杨林自己明明感觉颤抖的双手用尽了全力,但是打在张勇身上却像是不痛不痒。其实旁人看得清楚,此时的杨林已经根本用不上劲儿了,只有杨林自己不清楚。
张勇见自己羞辱地差不多了,一个箭步上去从侧面贴近杨林,用手臂环住杨林的脖子,脚下轻轻一绊,将其摁倒在地,然后用虎口狠掐住杨林脖颈两边的动脉,令其躺倒在地不能动弹。
南方士子纷纷叫好,北方士子终于恼羞成怒。
杨骏看那杨林根本不是张勇的对手,心中大为不悦,他叫过身边的斗魁,低头嘱咐了几句,斗魁点点头,叫来一个驺虞骑侍卫,那侍卫一跃上台,目视张勇,准备与之一战。
张勇突然感受到一股充满敌意的压迫感,这是只有身经百战的人才会有的感觉。他放开杨林,那杨林喘了几口气,本能地爬起身踉跄着逃下了台。
张勇转身看着眼前这个对手,身材魁梧,衣着并非一般的侍卫,低颅、阔面,样貌上并不像一般的北方人,双臂看起来孔武有力,最让张勇感到奇怪的是,他感觉对方在努力隐藏着杀气。
那侍卫一上来就伸出手指,指向张勇,是故意挑衅之意。
张勇心中怒火未消,恨不得把北方的晋人统统打倒在地,此时又见来人挑衅,不禁怒火中烧,于是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打过去,没想到对方竟然故意不躲,任凭张勇挥拳打在自己的身上,大有蔑视之意。张勇吃了一惊,以至怀疑起了人生,对方趁机出手,一拳将张勇打倒。
这一次换作北方人皆叫好,南方士子默不作声。
张勇挨了一拳,伤得不轻,却强撑着与对方拉开距离,以免二次受伤。那名侍卫继续伸手挑衅,羞辱张勇,张勇怒从心起,顾不得自己身上受的伤,起身猛冲上去,虚晃一招后迅速绕到对手背后,一把将那侍卫抱住,想以力搏将他摔倒在地。不料对方双膝一弯,不知用了什么招术,竟似有千斤之重,张勇根本没有办法将其扳倒,接着那侍卫将张勇双手掰开,一个背摔,将张勇从肩头翻过,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继而抬起手臂,一记直拳奔张勇头头部挥去。
汝南王见势不妙,只恐张勇被打死,刚要起身喊停,却只见一个硕壮的身影冲上高台,一把抓住那侍卫的手臂,那侍卫根本不顾来人,还要挥拳打去,然而自己用尽全力,手臂却无法挣脱出来,那侍卫面露惊异,回头一看,只见来人身高九尺,膀大腰圆,目光如炬,那手臂比一般人的大腿还要粗,自己用尽全力的一拳被他轻易止住,稳如泰山。他不知道对方是谁,只知道此人绝非等闲之辈。
来者不是别人,乃是被东吴称为“武神”的周处。
那名驺虞骑侍卫看着周处的眼神,心中倒吸一口凉气,不觉间流出了冷汗。
周处看了张勇一眼,张勇会意,乖乖退出场外,周处故意松开那名驺虞骑侍卫的手,自己则像毫无防备。
那驺虞骑侍卫知道此人乃是强敌,此时自己与他只相距半步,他见周处没有摆好架势,索性趁机出手,使出全力一拳打在周处身上。周处没有躲,任凭这一拳打在自己的身上,一拳到肉的声音不大,力道却十足。周处挨了这一拳,脚下却纹丝未动。
那驺虞骑侍卫见自己全力一击没有将其打倒,心里吃了一惊,心下发狠,又一拳朝周处的头部打去,周处见他如此阴狠,一伸手便握住了对手的拳头,轻轻扭转手腕迫使对他扭过身去,然后一手抓住他的衣领,一手抓住他的腰,像扔麻袋一样将他扔出了场外。
南方士子见周处为他们争了气,无不称赞叫好,只有陆机、陆云两兄弟始终不动声色。
“你……”杨骏大怒,将手中酒杯一扔,站起身,未等杨骏开口说话,从大门外走进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的脖子上戴着五彩丝系着的五彩凤凰珀,一进门就大声说道:“南方北方都是一朝之臣,一家之人,哪里有自家人打自家人的道理呢?百姓要是知道了,怕是会笑话!皇上要是知道了,一定会生气!”
这两个孩子不是别人,说话的是汝南王的小儿子司马瑾,另一个则是当今太子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也是武帝司马炎寄予厚望的晋国未来的皇帝。
汝南王司马亮平日十分宠溺幼子司马瑾,今日会集百官名士,不期司马瑾竟然会在此时走进来说出这样的话,似怒非怒道:“瑾儿,这在座的叔伯都是你的长辈,你如此莽撞地走进来,难道不知道行礼吗?”继而对众宾客介绍道:“众位见谅,这是本王的小儿子司马瑾,平时疏于管教,有礼数不周之处还请见谅!”
杨骏问司马亮:“司马瑾?莫不是羊太傅取名的那个司马瑾?”
司马亮笑道:“正是!小儿年幼无知,言行鲁莽,请不要见怪啊!”
“哪里哪里,我看他举止不凡,有胆有识,可谓虎父无犬子啊!”
卫瓘点头笑道:“此子生而不凡,今观其言行亦不凡,不枉羊太傅一番厚爱为他取名啊!”
荀勖也道:“汝南王说他鲁莽,我却看他颇有气度,且很有见识,料日后必成大器!”
司马亮大悦,站起来说道:“多谢诸位的包涵和赞赏,今日本是皇上降旨,命本王在府上设宴召集南北名士,相互交流,天下分裂已久,南北隔阂颇深,此为天下之不幸。天下既然统一,就不应该再有南北之分,拳脚打斗易伤和气,比武一事,暂且作罢吧!”
“也好也好。”
杨骏哪里受过这种气?本想发作,怎料被一个孺子打乱,汝南王司马亮又顺势制止了比武一事,众人点头称是,自己就更加不能反驳,所以杨骏把本来想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众人见汝南王拉出了皇帝的名义,不得不听命于他,纷纷赞同,杨骏心中虽有气,只得忍耐道:“好,那就聊聊文章吧!”
谈至文章,此时的左思,琢磨十载,写得《三都赋》,使得洛阳人士争相传抄,一时竟出现洛阳纸贵的盛况,左思也从过去经常被人嘲弄的小小秘书郎,摇身一变成为晋国第一才子。北人推崇左思的《三都赋》,而南方士子则拿出陆机的《文赋》,并说陆机的文采高过左思。
左思、陆机二人却不说话,其他人倒是越争越厉害,非要分个高下。这个说《三都赋》冠绝古今,那个说《文赋》一出再无文章。司马亮有心平复众人争论,怎料这些文人文斗起来比武斗还要激愤,且司马亮自己对这些文章不过略知一二,真要让自己说,却也说不出什么来。
杨骏笑着对司马亮说道:“都说文人相轻,果不其然啊!”
司马瑾站在一旁没有说话,卫瓘见司马瑾小小年纪似有睥睨天下文士的气度,奇之,待两边争过气后,问司马瑾:“司马瑾,你可读过《三都赋》和《文赋》?”
卫瓘博学而谦卑,无论南北士子都对他敬重有加,所以卫瓘一说话,众士子皆缄默不语,又见卫瓘问司马瑾文章之事,无不好奇着洗耳恭听。
“读过!”
“哦?”卫瓘点点头笑问道,“刚刚众人对这两篇文章争论不休,你怎么看呢?”
司马瑾答道:“我觉得《三都赋》和《文赋》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争议啊!”
“你的话可有依据?”
“当然有!《三都赋》里有一段话写道: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而《文赋》中也有一句话的观点与此相似: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我还记得左太冲先生(左思)曾说过,自己写的诗中,最喜欢的只有两句:‘士胄蹑高位,英俊沉下潦。’这两句诗之所以好,正是因为‘缘情而咏志’,可见真正的文人只有所见略同,而不分高下。至于‘文人相轻’嘛……”司马瑾看向其父司马亮欲言又止。
卫瓘道:“大胆说来,没有关系!”
司马瑾见有人给自己撑腰,继续说道:“其实真正的文人是不相轻的,‘文人相轻’出自曹丕的《典论》,其实曹丕的诗赋与曹操和曹植比起来,写得很一般,他对弟弟曹植,是有嫉妒之心,所以才说‘文人相轻’,因为他是皇帝,一言九鼎,时人惧怕他。因此‘文人相轻’这句话才流传了下来!”
在座众宾客没有谈论观点对错,只是对此子有如此见识,纷纷赞许,卫瓘笑着没有说话。
汝南王司马亮道:“稚子孩童,能懂什么?这些不过是你的臆断,就敢在众名士面前胡说?天下名士这么多,只有你说那曹丕是错的?大家不与你争,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对的了?不过看你年纪小,不愿与你争论罢了!”
皇孙司马遹笑着看了司马瑾一眼。
司马瑾答道:“有理有据,怎么能说是我胡说呢?”
卫瓘问:“哦?理据在哪?”
司马瑾道:“我听说陆士衡刚到洛阳时,也想写《三都赋》,后来看到左太冲的《三都赋》后,赞不绝口,再不提此事了,他们是真的文人,然而没有相轻!”
卫瓘问陆机:“士衡(陆机),是真的吗?”
陆机挺起身笑答道:“是真的,我还曾给我的弟弟陆云写信说,北方有一个粗鄙之人,也想写《三都赋》,等他写成之后,我将用他写的文章来封盖酒翁呢!”
众名士听罢,都哈哈大笑。
陆机接着说道:“等我看到左太冲的《三都赋》后,确实叹服!我若再写,只是取辱,于是我就搁笔不写了。”
卫瓘道:“果然是英雄惜英雄,名士惜名士啊!”
此时在座的名士也有见拙的,也有看汝南王的面子称赞司马瑾的,南北名士纷纷言和,再不提‘文章’二字。
杜预见刚刚还争得面红耳赤的文人名士,因一孺子而解怨释怀,不禁开玩笑道:“我记得此子字徵羽,如今长大,定弹得一手好琴,既逢宴会不如弹奏一曲如何?”
司马瑾见是杜预问话,忙答道:“瑾虽对音律十分喜爱,却一直没有名师教导,虽略知一二,却不精通。”
杜预笑道:“这有何难?今日天下名士聚集于此,还怕拜不得一位师傅吗?我听说士衡(陆机)、士元(陆云)琴艺精湛,不如今日收下这孩子为弟子!”
陆机、陆云闻言连忙作揖,只说自己何德何能?众名士笑他二人谦虚,定要他们弹奏一曲。陆机推脱不过,只得接过琴来,抚琴闭目正身以待,众人见状纷纷如钟而坐,静而不语,鸦雀无声。
一阵清风吹过,此时园内只有风动、草动、水动,仿闻枝摇、叶落,又似有湛湛水波。陆机睁开双眼,轻轻一拨,音弦长荡,余音不绝,继而缓缓而弹,有如锦缎缠绵,愈收愈紧,杂乱却有章,其间轻、重、缓、急、快、慢、放、收,使得一曲之音,其情饱满,令人闻之忘他,忘我,忘一切事,身坐于地而遐想于天际,迷醉其中而不自觉。
一曲奏罢,余音犹在,众宾客却仍陶醉其中,连司马亮、杨骏也都闭上眼睛,摇晃脑袋。慢慢的,人群中渐闻泣涕之声,恍惚间哭声荡于整个庭院,众人惊醒,寻声望去,只见一老者伏于案上痛哭流涕,众人寻声望去,竟是山涛山巨源。
没人知道山涛哭的缘由,旁人只得劝慰一番,哪知越劝他越是哭得厉害,哭得放肆,起先只是伏案而泣,待嵇绍扶起他,他竟抱住嵇绍痛哭不已。众人见山涛如此悲怆,听着有如心割,有的竟也跟着悲伤起来。
杨骏见山涛无故痛哭,大觉扫兴,心里本来烦闷,借说府中有事,于是跟汝南王告辞离开。斗魁跟在杨骏身后,临走时,目露凶光地看了周处一眼,周处觉察到了斗魁的敌意,那不是普通的杀意,那目光冷酷无情似乎嗜血成性,令人不寒而栗。
汝南王司马亮见山涛太不成体统,只得命人扶山涛进内室休息。
山涛既走,有人摇头,有人叹息。有人说他可能是想起了嵇康,否则怎么会抱住嵇绍不放呢?有人说可恨嵇康无情,可叹山涛有义,嵇康当年写了那篇著名的《与山巨源断交书》,哪知山涛不仅没生气,还在嵇康死后收养了他的儿女,并举荐嵇绍做了官,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刻薄,一个海涵。大家都十分赞赏山涛的为人。
待司马亮处理好山涛大哭一事后,继续主持宴会。无论南北名士,皆赞陆机曲妙。汝南王见南北名士终于不再争辩,满意地捋须颔首而笑。
张华问陆机:“此曲美妙,有如甘味,食之不厌,我竟从未听过,不知曲为何名?”
陆机拱手作揖道:“方才我忽然回忆起年少时与家父在华亭度过的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家父最喜白鹤,每日只闻鹤声、水声、琴声,十分自在,此曲就是家父教给我的,至于名字嘛,家父也没有说。如果陆机失礼,还望不要见怪!”
“哪里哪里!”司马亮由衷而言:“士衡乃真名士!才华横溢,实在令本王佩服!若士衡愿意,就收下我这个小子为弟子,如何?”
陆机哪敢推脱,谦逊推脱不才一番后,终于当着众名士的面,收司马瑾为弟子。之后陆机让司马瑾拜识周处,原来这周处与陆机也有师生之谊,不过周处只随陆机学文。
司马瑾拜完陆机,陆机夸赞道:“我见小公子出口成章,见识不凡,想是有名师所教?”
司马亮大笑道:“哪里有什么名师?他自小体弱多病,本王想让他多读些书,但是他自己却偏偏喜爱骑马舞剑,教他剑术的老师也夸他有用剑的天赋,他也懒于读书,所以也没有给他找什么名师,平时他不过跟着族中弟子一起读书而已,不过我常闻夫子夸赞他,也不知是真夸赞,还是奉承我,也就没当一回事,有一日我与宾客谈到曹植的《洛神赋》,他说可以背咏,我不信,不想他果真背得一字不差,我方信夫子说的是真话。”
陆机点头道:“小公子聪慧,他的学识胆识在同龄人中拔乎其萃,我像他这么大时,远不如小公子!”
宾客们纷纷点头称赞,汝南王司马亮大悦,举起手中酒杯与众宾客共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