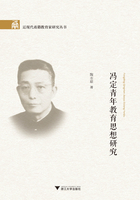
第二节 出生于望族的衰微之家
冯定家自次牧公以后就开始衰微,到他的曾祖父辈便已靠做手工讨生活了。冯定的祖父冯金福,既是厨子又是漆匠,冯定的父亲冯慎余也是又做厨子又做漆匠。冯定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51岁,母亲已经39岁,可谓老年得子,可他们的心情却是喜忧参半。
一、排行老八的冯远龙出生了
1902年9月25日,对于浙江省慈溪县(今宁波江北的慈城)的一个普普通通的、靠家中男子当漆匠和厨子养活一大家子的冯氏家庭来说,既是一个高兴的日子,也是一个略带忧愁的日子。说它是高兴的日子,是因为冯家虽然已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但又增添了一个儿子,可谓是四双儿女,对于深受“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思想影响的冯家来说,添了一口人当然是喜事了;说它是个略带忧愁的日子,是因为冯家一直靠干漆匠活和做帮人办酒席的厨子为生,本已家境清贫,再增添一张嘴吃饭,只会平添压力。然而,这忧愁只是皱了皱眉、轻叹了口气般一带而过,新的生命带给这个家庭的新的希望是无法掩盖的。于是,母亲乐滋滋地盯着这个弱小却充满了生命活力的小东西,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小儿子侬要乖乖的,阿拉家翻身就全靠牢侬了……”父亲也默默地坐在堂屋里想着自己的心事:“虽说这家里又要添一张嘴吃饭了,不过吾家这老八,一定会顶呱呱的,一定会光耀门楣、光宗耀祖的……”想到这里父亲浑身充满了干活的劲头。怀着这种期望,父母为这个排行老八的儿子取名“远龙”,期望他成为有远大志向且让父母引以为豪的人。
冯定年幼时,邻居家的孩子和学童们都叫他“漆匠阿慎的儿子”。冯定的大哥冯寿龙比冯定大五岁,也是漆匠,同时也是苦力,长期替有钱人家做杂工,有时还要挑很重的担子。冯定家住的是布政房的老屋,但后来只留下一间当作前后宅穿堂旁边的房子了。本来尚有五六亩祖田,但已直卖(直卖,在名义上是卖,但仍可赎回,相当于无限期的抵当)给原来耕种这些土地的姑母家了。此外,作为布政使的后代,也还有很多祀田可以轮值,不过扫墓、设祭、分胙等项目的开支花费也很大,所以大家并不太爱轮值祀田;但因为冯定的父亲自己是厨子,母亲和大哥又能劳作,所以轮值时也多少有所收获。就这样,冯定家不但因为人丁少而经常得到三年一次的轮值,而且别人家也还经常委托冯定家轮值。冯定幼时的生活,主要是靠父亲和大哥的劳动来维持的。冯定的父亲于1916年去世,那时冯定才14岁。冯定的母亲也是贫家女儿出身,在1926年也去世了。
二、兄弟姐妹虽多但各自命运不济
冯定有三个哥哥和四个姐姐。冯定的大哥冯寿龙和父亲曾经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支撑起这个家庭。但冯定的大哥比父亲还早死数年。冯定的大哥患的是肺病,完全是因为过度劳动,但一直未能医治,最后已无法抢救,在病榻上呻吟二三十天后痛苦而死。虽然父母为大哥取名“寿龙”,却未能保证他长寿,可谓“寿龙不寿”!冯定的二哥冯友龙,十岁时就到僻陋的嵊县(今嵊州市)的一个小首饰店里做学徒。父亲临死前不久,才由族人介绍至苏州的大铺子里当匠师。那个时候,冯定的父亲已经不能进行太多的体力劳动了,幸亏二哥已经能够寄些钱回家帮补家庭,解决一家的生活问题了。但二哥的思想比较闭塞,对冯定进学校读书一事怎么都看不顺眼,认为父亲对长子、次子过于严厉而对冯定有太多的偏爱,因而从小和冯定就不和睦。对于冯定而言,二哥虽然叫“友龙”,可对自己却并不友好。冯定师范毕业后,由母亲做主分了家,从此开始独立谋生了。事实上,冯定从此就离开了这个家庭。后来,二哥将原已直卖的几亩田地赎了回来。在1930年前后,二哥回家摆小摊、开小铺,经常承值远祖的祭祀。冯定的三哥叫冯文龙,十一二岁就到上海一家王金铺子学做生意,也因为得了肺病,和大哥在同一年里相继死去。
冯定的大姐嫁给了一个名叫陈寅兰的小贩。陈寅兰开了个小铺贩卖东西,但他却死得很早,留下妻子和几个儿子独自生活。大约从1925年起,大姐和几个儿子就一直在上海开一家小百货铺子维持生活。1934年至1937年间,冯定经常租用大姐楼上的空房住,并且把其当作转信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冯定大姐的小铺已经关闭,大姐的长子陈长生,由冯定介绍至华东猪公司做事;大姐的幼子陈翼生,在工人合作社做事,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冯定的二姐嫁给了一个农民,生了一个女儿后就自杀了,二姐的丈夫和他们的女儿没过多久也都死了。冯定的三姐嫁给了一个姓曹的厨子,但三姐和她的丈夫均死得早。新中国成立后,三姐的儿子曹瑞春,经冯定介绍在上海一所小学里教书。冯定的四姐嫁给了一个中药铺的司账,在浙江衢山镇过着还算平静的生活。
在这样有些凄苦的家庭环境里长大,这不免使冯定很早就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不满。由于大哥和三哥的早逝、二姐的自杀,再加上冯定本身的体质较弱(因先天不足和后天缺乏营养而一向非常衰弱),所以他自幼就有一种消极而又倔强反抗的意识,从小就有“死了也就一了百了”这样不健康的思想,甚至在幼时就想过自杀。冯定尚在小学的时候,曾因为一件小事而被父亲无缘无故严加责罚,冯定觉得受了委屈,便喝了一大匙盐卤试图自杀。他喝了之后感觉胃痛难忍,幸亏旁边有凉开水,连续喝了好几杯才终于消解了胃痛的症状。
这种“死了也就一了百了”的消极思想对冯定后来的人生产生了一些影响,比如说冯定有时想得很远,而对眼前的具体工作却提不起精神去做。这种消极思想,特别是在与同志交往时,如果不被谅解或者感觉受了委屈,就会产生严重的抑郁情绪,以至于冯定有时候只是消极忍耐,心里想只要知道自己没有过错就行了,这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想法,让他失去了主动、积极地去调整人际关系的热情。但这种思想也有积极的一面——面对敌人无所畏惧,因为冯定觉得大不了就是一死,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由此看来,凡事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正面的影响看那就是,对非原则性的问题能够持比较豁达、大度的态度。
三、聪明好学的小远龙在失望中有了希望
冯定出身贫寒,童年的生活非常清苦。冯定的童年、少年时代均在故居——布政房前宅穿堂旁的一间房子中度过。从1908年春至1913年夏在初等小学上学,从1913年秋至1916年夏在高等小学上学,都是走读。1908年春,不过才五周岁半的冯定就开始在慈城冯氏家族开办的小学(政婉小学)读初小了,到1916年夏,冯定在这所家族小学读完了高小。冯定读初小和高小期间,无须交付学费。原来布政使有个家庵,也有田产,当清末废除科举办学校的时候,冯姓中有些开明士绅,在征得冯定父亲的同意后,将家庵中不守清规的尼姑驱逐出去,借此开办了慈城唯一的女子小学,因而规定了冯家子弟今后都可免费到冯定家附近的小学去上学。冯定在初小和高小读书时一直都非常认真和用功,在心里暗自发誓长大后要像族叔冯君木那样成为有学问的人。冯定的用功深受老师的喜爱和同学的羡慕。冯定在上小学期间曾参加过庆祝辛亥革命的提灯会,唱过“天下荣,丈夫争战功;天下乐,英雄破敌国”这样的歌。也许就是这“天下荣”“天下乐”的思想观念扎进了冯定幼小的心灵里,使得他后来的人生能获得较大的成就吧。由于当时冯定的家境实在贫寒,小学毕业之后,冯定虽然向往进一步的求学之路,父母却无力支撑他的升学愿望。正当远龙深陷“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失望时,却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