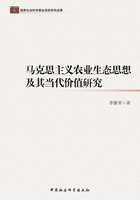
第二节 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手稿中蕴含的农业生态思想
1848年以前,马克思把注意力放在从哲学上论证科学共产主义,1848—1849年致力于政治思想的研究,而在五六十年代则把经济学说的研究提到首位。1850年年底,马克思恢复了他早在40年代就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的研究工作。从马克思准备写作时所做的笔记可以看出,除了研究经济科学本身外,他还广泛研究了许多有关技术史、文化史、数学、农业化学的著作以及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使他感兴趣的其他科学著作。
50年代的研究中,包含了马克思农业生态思想的文本除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导言、序言外,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政论文章中也有多处涉及对农业问题的分析,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另外,从这一时期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书信往来中,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已经比较关注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研究。在研究地租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搞清楚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便促使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有关农业生产问题的各方面进行了广泛的阅读。对马克思在50年代的主要著作和手稿及书信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此时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农业问题等的分析,穿插渗透在马克思对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等问题的分析中。在对有关问题进行分析时,马克思经常以农业为例来进行说明,但正是在这点点滴滴的分析中,总结下来却包含了丰富的农业生态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人与自然关系的进一步论述及对“物质变换”概念的全面分析
(一)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对自然的占有和支配,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37]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进行了论述,这里对资本主义之前的一些所有制形式的论述中有一些关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思想值得关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已经基本上从物质生产的意义上来进行阐释了。
马克思认为,人类要生存,首先要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土地、自然界既为人类提供劳动资料,又为人类提供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在“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中,马克思认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38]在“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中,马克思同样表达了土地对人类生存和生产的这种重要作用: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39]在《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在古代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在共产主义下的财富》的分析中,马克思再一次指出: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40]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客观条件,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
(二)“物质变换”概念的论述
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中,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思想可以说是其生态思想的核心。在1858年8月到1859年1月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这一思想已经得到了较充分的阐述。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是在两种意义上来阐述“物质变换”思想的,一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正如马克思自己在1879年下半年到1880年11月所写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明确指出的一样,马克思认为,自己在说明生产的自然过程时使用了“物质变换”这个名称,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在分析W—G—W(商品—货币—商品)时,也使用了物质变换,而以后形式变换的中断,也是作为物质变换的中断来说明。[41]
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马克思对之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人类劳动进行了这样的论述:劳动作为以某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同一切社会形式无关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条件。[42]这是马克思第一次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意义上来认识劳动。
而商品以货币为媒介与其他商品之间的物质变换,正是马克思之前研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为了说明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交换,多处使用了“物质变换”这一概念。马克思认为:商品交换是这样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物质变换即私人特殊产品的交换,同时也就是个人在这个物质变换中所发生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生。商品彼此间在过程中的关系结晶为一般等价物的种种规定,因而,交换过程同时就是货币的形成过程。表现为种种过程连续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整体,就是流通。[43]而买和卖在交换过程中的分裂,破坏了社会物质变换的地方的、原始的、传统虔诚的、幼稚荒谬的界限,它同时又是社会物质变换中相互联系的要素彼此分裂和对立的一般形式。[44]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谈到商品和商品之间的交换时用“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代替“社会物质变换”这一概念,更明确地指出社会物质变换其实质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的关系。马克思说:W—G—W,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W—W,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45]由此可知,马克思对“物质变换”的分析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但他对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使用了“社会物质变换”或“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来表达,而将“物质变换”这一概念主要用于分析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
显然,尽管马克思的研究重点放在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其学术语言也更多地转变为经济学语境下的研究,但这里“两种和解”的哲学思想仍然是马克思致力要解决的问题。马克思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则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就要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入手,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科学的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同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解决也要从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变换入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互相影响的。这些都与马克思之前的“两个和解”的思想是一致的,只不过是更深刻意义上的分析,但相比较而言,这个时期的分析还不够系统化。
二 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资本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资本”章里,马克思提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资本的社会影响也表现在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上。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英国,由于尼德兰商品的输入,用于交换的剩余产品羊毛销路非常好,于是,为了生产更多的羊毛,耕地变成了牧场,土地的用途发生了变化,这是由资本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利润原则决定的。所以,马克思说: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而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对于农业的内部结构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在某些地方,农业本身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46]在一些国家里,例如荷兰,旧土地所有权解体的过程已经完成,农业已经为畜牧业而牺牲,而谷物则从落后的国家例如从波兰等等进口。[47]
资本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表现在从土地制度上看,小租佃制也遭到了破坏,发生了清扫领地等行为。马克思说: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从某一方面来看,资本表现为现代农业的创造者。[48]
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小租佃制遭到破坏,土地集中,这就使无地农民、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茅舍贫农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49]这部分“土地上的过剩人口”被土地所有者清扫出土地,马克思说,资本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50]这意味着现代农业与土地所有权的集中相联系,与土地上人口过剩相联系。而这一土地上人口过剩问题的产生及其流动问题,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农业生态的变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资本在农业生产领域的使用促进了现代农业生产方式的发展,现代农业有利于农业科学的利用,有利于土地生产力的发挥,有利于人类从有限的土地上获得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而这也正是资本、土地、农业生态之间互动变化的过程。
(二)土地所有制
1.小土地所有制不利于农业分工和农业科技的利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于1851年12月至1852年3月,是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分析了当时法国的社会状况和法国农民的生活状况,其中的分析包含了一个结论,即小块土地耕作不利于农业分工,不利于农业科技的利用。马克思说: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51]
2.对土地垄断的批判
在1853年6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一文中,马克思借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之口批判了土地的垄断。首先,马克思认为,李嘉图以“更简单、更科学因而也更危险的办法攻击了土地垄断”,李嘉图证明了土地的私有制不同于农业工人及农场租佃者的相应的要求,土地私有权是一种完全多余的、同现代生产的整个制度不相容的关系。马克思说:如果要把李嘉图学派从反对土地垄断的这些前提中所得出的所有结论一一列举出来恐怕令人不耐烦。从我的目的来说,只要引证政治经济学方面英国的三个最近的权威的话就够了。[52]接下来,马克思引用了《经济学家》报纸的观点、纽曼及斯宾塞两位先生的话来进一步表明自己反对地主对土地的垄断的观点。伦敦的《经济学家》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一直肯定地认为,不可能允许任何个人或某些人有要求独自占有国家土地的权利;纽曼先生在《政治经济学讲演集》中肯定:任何个人,只要不亲自经营土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天然的土地权。他的权利只涉及使用土地,此外再没有什么权利。[53]斯宾塞先生则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有这样的阐述:谁也不能因自己享用土地而阻挠其他人同样享用土地。因此,正义不允许占有土地,否则其他人就只有得到占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活在大地上。没有土地的人甚至被人家以权利为理由从土地上赶走……妄谈现有的这种财产权利合法,从来都是没有根据的。……土地不应当是个别人的财产,而应当属于大团体——社会。务农的人不应当向个人占有者租佃地块,而应当向国家租用。不应当向约翰爵士或公爵的代理人交地租,而应当把地租交给社会的代理人或下级代理人。[54]在引证了这三种说法以后,马克思说:“由此可见,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55]
马克思此时还没有对土地所有权进行系统的分析,也没有从对农业生态的影响上来对土地所有权进行任何评价,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小土地所有制和对土地的垄断不利于农业分工和农业的科技的利用。这一思想在60年代通过地租理论的完善而得到了系统阐述。
(三)政权制度因素
马克思1856年11月7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社论《法国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文中将话题从交易所、铁路、商业和工业转向了法国的农业。马克思认为,法国当年的歉收比法国关税报告书所公布的状况要严重得多,指出:如果认为促使法国明显地从谷物出口国变成谷物进口国的原因仅仅是水灾、恶劣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现象,那将是错误的。[56]马克思认为,法国农业的严重困难既是自然灾害的结果,也是目前政治制度的产物。法国的农业在现存政权下确实是衰退了,衰退的原因是由于一方面,我们看到税收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不断减少(大量劳动者因战争而暂时离开了土地,因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而长期离开了土地),同时资本被愈来愈多地从农业中抽去经营投机事业。……帝国贷款把交易所搬到农民的茅屋里,榨干了他们的私人积蓄,刮走了从前用于改进农业的小额资本。[57]无论是税收还是劳动力的减少或是资本的减少,都与现存政权有关。这足以说明,自然现象对农业生产状况的影响是一方面,但是人为的影响会在自然影响的基础上对农业生产产生很大的作用。
(四)土地改良与农业科学技术
50年代,马克思大量阅读有关农业化学方面的书籍,在这一时期谈到有关农业生产的问题时,已经能就农业方面的改良和农业科学技术的利用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尽管对一些问题的论述还远远不像《资本论》中那样成熟。
在1853年6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社论《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中,马克思在谈到印度的“租佃权法案”所规定的租佃者和地主之间就土地和土地之外所进行的改良而应得到的补偿问题时,进行了这样的分析:在租佃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把资本投入土地,因而改良了土壤以后(这种改良或者是直接的,如灌溉、排水、施肥,或者是间接的,如农用建筑),地主就插了进来,要租佃者出更高的租金。如果租佃者让步,结果就是他用自己的钱,而给地主利息。如果他坚持不肯,那么他就会被人不客气地赶走,换上新的租佃者,新的租佃者由于接受了前一个租佃者投入的费用,于是就能够付出更高的租金了;新的租佃者也改良土地,结果是照老样被另外的人代替,再不然就是处于更苛刻的条件之下。[58]这里,马克思认识到由于土壤的改良在地主和租佃者之间产生的矛盾。但是,这时马克思还没有进一步认识到这种矛盾对于农业生态产生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也提到了关于土地的改良。此时,马克思对土地改良的认识已经不仅仅像1853年所认识的那样认为土地的改良要么是“直接的,如灌溉、排水、施肥”,要么是“间接的,如农用建筑”,马克思进一步从农业化学的角度来认识土地改良,他认为,土地改良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从而直接变成使用价值[59]。当然,在农业中建造水渠仍是非常必要而又基本的改良活动,在此基础上,有一部分谷物被用去交换鸟粪,交换化学物质等等,这些东西施在土地上,但实际上它们只有纳入化学过程才有使用价值。[60]
研究农业生态思想,研究农业生态的变化,研究现代农业的发展,一定不能离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50年代初期,马克思为研究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从而提出自己的新地租理论,就已经非常关注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了,对于农业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些新的技术,马克思总是要搞得一清二楚。1851年5月5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附有一份关于农业中应用电的文章的抄件,马克思请恩格斯谈谈对农业用电及农田架电杆问题的一些看法。1851年5月9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对此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其中谈道:如果电对植物的发芽和生长具有积极的作用,那么它就会使植物春天发芽过早,并使植物受到夜间霜冻等等的威胁。这种情况无论如何是必定会发生的,只有在冬天把架空的导线和地下的导线都截断才能补救。[61]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就农业生产中使用电来促进植物的发芽和生长的一个实验来发表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后来没有进一步的讨论,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过程中,已经不是完全依靠自然力作用于农业生产了,人类可以通过物理的、化学的等措施来改变植物的生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利用这些措施来对植物的生长施加影响的同时,也会出现一些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控的影响。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有了初步论述。马克思认为,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科学的发展足以改变社会的经济条件及政治关系。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62]科学是一种观念的财富,即无形的财富,同时科学又是实际的财富,因为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能带来财富的增加,所以,科学的发展就是人类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马克思表达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在工业发展中,财富的生产越来越取决于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在生产上的应用。马克思指出,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
(五)水利设施
对水利设施的分析,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东方农业生产的分析来进行的。1853年6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分析和总结了东方农业生产的特点。[63]
由于特殊的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得东方的农业生产必须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等人工灌溉设施。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64]这种对水利设施的需求在西方会由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来提供,而在东方社会,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65]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亚洲,政府部门有三个,即负责对内进行掠夺的财政部门,负责对外进行掠夺的军事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是亚洲国家非常重要的政府部门,因为,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66]通过对东方国家的考察,马克思看到了东方农业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即政府为农民的农业灌溉提供水利基础设施。正是因为东方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水利设施等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当不列颠人在东印度进行统治的时候,由于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而让东印度的农业像西方农业一样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进行生产,结果使东印度的农业变得衰落下来了。但是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67]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对东方国家农业的研究,直到现在仍然对我们有重要启示。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把水利事业的发展提到了重要战略高度,这意味着在我国水利设施的建设仍然是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1853年7月22日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归纳了对印度的看法。不列颠的工业巨头们发现,把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因为在印度由于极度缺乏运输和交换各种生产品的工具,所以它的生产力陷入瘫痪状态。印度的自然物产是丰富的,但是,由于缺乏交换的工具却使社会非常穷困。比如在印度出现某一个地区的小麦非常便宜,但是因为泥路不能通行,粮食无法运输,而另一个地区却非常昂贵以至于那里的居民正饿死在大街上。因此马克思说,铁路的铺设可以用来为农业服务。不仅是在运送粮食方面为农业服务,还可以在其他方面为粮食服务。例如在筑路基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的地方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需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地方饥荒的现象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的山区,只要是灌溉的土地,就比面积相同而不灌溉的土地多纳两倍的税,多用9—11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益。[68]马克思认识到在需要灌溉的地区,水利事业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提倡通过水利事业的发展来改善农业。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利用修建铁路取土之便来修建水库,这一将运输业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发展相结合的思想,实际上是其后期提出的“循环经济”思想的早期不成熟的表达。我们知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通常都会对周边农业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提出了可以利用修建铁路取土的机会顺便兴修水利,这种思想对我们现在维持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仍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六)季节性因素
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马克思在这里以农业生产中的资本流通为例来说明资本的回流与生产的特点有关,为了说明这一问题,马克思对农业生产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即农业生产有季节性。马克思说:在某些生产部门——农业中——还取决于由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劳动的中断时期,在这种时期,一方面资本闲置不用,另一方面劳动也停止下来。[69]农业生产过程本身的特点,反映出农业劳动力使用的特点,马克思对农业劳动特点的分析,对我们现在认识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有帮助。他说,例如,在牧场上饲养牲畜使用的劳动很少。另一方面,在农业本身,例如在冬季使用的劳动很少。在农业中(其他一些生产部门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会引起劳动时间的中断或停顿,而在一定的时候又必须重新开始劳动以便继续进行或完成生产过程。[70]这就意味着在农业生产中存在季节性劳动力转移问题。
三 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
(一)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谈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意义和基础地位。在《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在古代世界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在共产主义下的财富》的分析中,马克思说: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71]马克思在这里明确指出农业是各种所有制形式下经济制度的基础,这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给予了充分肯定。
(二)农业的发展及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关系
在分析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时,马克思认为,农业生产领域最能说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问题。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是最直接的对自然的改造过程,农产品的生产不仅是在原来的形式中再生产,而且是适应人的需要而改变了它的自然存在本身。[72]由于农业生产无法摆脱自然力的作用,因此,从价值生产的生产率来看,农业部门比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但是,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能够直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从这一点来说,农业比其他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高。然而,只有在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般生产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这种情况本身才能有利于农业。[73]马克思认为,由于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即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必然有差别,农业生产产品完成前,必然要有劳动中断的时间,因此农业不是资本最初所选择的获取利润的领域。只有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作用,资本才能掌握农业,农业才能工业化。[74]即工业化农业的出现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对农业发生作用的结果,是资本在农业领域里发挥作用的结果。而这种农业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竞争有高度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化学、力学等,即要求制造业有巨大的发展。这一方面说明工业化农业的起源,另一方面说明了农业发展与其他行业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
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农业部门内部的关系包括种植业内部、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关系,还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消费活动中产生的废料是否又进入生产过程。分析农业生产部门内部的关系,对我们理解有利于农业生态改善的农业内部循环有帮助。马克思这样论述:在农业中,一部分产品(种子、牲畜等等)本身也是本部门的原料;所以,它们本身像固定资本一样永远不离开生产过程。供牲畜消费的那部分农产品可以看作辅助材料。但是,种子在生产过程中被再生产出来,而工具本身则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75]
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在离开消费本身时重新成为生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等等,用废布造纸等等。[76]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包括农业种植的粮食、畜牧业生产的畜产品等,通过人类的消费活动,这些物质与人体之间实现了“物质变换”,在离开消费本身时,已经是以人类消费排泄物的形式存在了,马克思认为这些“消费排泄物”重新成为生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在这里,马克思开始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思想及从自然界获取和归还的循环利用思想进行分析,但并没有明确给予论述。这一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了系统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时,分析了人类生产过程中“需要”的变化,蕴含了对农业和手工业、商业、工业等之间的关系的分析。马克思认为,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77]。由于农业的需要发生变化,相伴随的手工业、商业及工业也会发生变化。自给自足的农业是把纺、织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与此相并存的即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如果农业本身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农业中需要使用机器来进行生产,如果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种子需要从远方国家来获得,如果农业生产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78]可以看出,农业部门的发展会对其他部门的发展产生影响,或者说农业部门的需要的发展,会促使商业及工业部门为满足这种需要而得到发展。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而且,这种存在于农业之外的部门,连同这个外在的部门具有的那全部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成了农业的生产条件),主要地和基本地是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79]
四 关于人口与农业发展的相关论述
(一)人口的增加与土壤肥力的变化
在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初期,马克思对人口的关心也只是从物质资料生产的角度分析人口是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对物质资料的需求也会增长,从而会促使人类提高生产力。对于恩格斯在40年代就关注的马尔萨斯人口原理,马克思在40年代没有发表任何看法。到了50年代初期,马克思在研究地租理论时开始注意到人口问题与土壤肥力之间的关系。1851年1月7日,在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讨论了关于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人口对土地的要求越多,土地就变得越坏。土地变得相对越来越贫瘠了。马克思认为这一论点是与历史相矛盾的。他认为,随着文明的进步,人们不得不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由于科学和工业的进步,这种较坏的土地和从前的好的土地比起来,是相对地好的。
马克思在信中说:地租问题的根本实质就在于:地租是由于使不同的生产费用所得到的产品的价格平均化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市场价格规律不过是资产阶级竞争的规律而已。此外,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仍然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土地相对地越来越贫瘠,连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所创造的东西愈来愈少,虽然那时和在资产阶级制度下不同,最好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将不会和最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一样贵了。[80]马克思在这里指出,土地的越来越贫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土地肥力所产生的特有的影响,即使在资产阶级的生产被废除以后,未来的社会农业生产也同样会由于连续使用土地而使土地的边际产品越来越少。
对此问题,恩格斯在1851年1月29日给马克思的回信中指出,自己对李嘉图关于土壤肥力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递减的看法始终是不信服的,他认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完全忽视了农业的进步,并且恩格斯再次指出,自己曾在《德法年鉴》中用科学耕作法的成就批驳过肥力递减论的说法。1851年2月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说:我的新地租理论目前只是使我获得了任何一个老实人所必然追求的自信心。不过,无论如何,你对新地租理论表示满意,我是高兴的。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成反比……[81]关于土壤肥力和人的生殖能力的提法,虽然马克思没有展开说明什么,但显然表明了马克思认可土壤肥力逐渐下降和人口生殖能力提高的趋势。
(二)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
但到了50年代后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同时,阐明了自己的人口理论。马克思说: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82]因此,对人口问题进行分析,必须结合社会生产方式来分析。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83]
马克思辩证地看待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他首先指出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他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了资本的残酷的观点;另一方面,马尔萨斯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势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
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马尔萨斯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把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互相对比,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另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84]对于马尔萨斯的这种错误,马克思认为,在历史上,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决定的。
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荒谬之处还表现在:马尔萨斯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85]马克思指出,人口过剩并不是指人口相对于已有的生活资料来说过多了,而是因为这些过剩人口失去了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条件。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出现的过剩人口,并不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的生产方式有关。[86]
这表明了马克思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基本观点。过剩人口在历史上每个时期都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口过剩问题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人口过剩并不是指人口相对于生存资料来说出现绝对过剩,而是相对于占有生存资料的方式而言出现的相对过剩。所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不能如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通过战争等极端的方式减少人口的绝对数量,而是应该从改变生存资料的占有方式入手。
马克思说,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的增长规律。人口问题在当代有新的表现形式。人口按照其自然规律增长的同时,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率也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由于农业生态环境的恶化,全球粮食产量增长幅度逐渐减缓,从长期发展来看,粮食问题正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一粮食安全问题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当代的人口问题,另一方面要从农业生态环境入手,解决粮食生产持续增长遇到的危机问题。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3] 同上。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5] [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
[8] 同上。
[9] 同上书,第96—97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03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14] 同上书,第122页。
[15] 张一兵:《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日]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代译序。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注释。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页。
[18] 同上。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1页。
[20] 同上书,第24页。
[21] 同上书,第31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23] 同上书,第35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3页。
[25] 同上书,第35页。
[26] 同上书,第43页。
[27] 同上书,第5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8页。
[30] 同上书,第457—458页。
[31] 同上书,第190页。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25页。
[33] 同上书,第56页。
[34] 同上书,第26页。
[35] 同上书,第57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9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38] 同上书,第472页。
[39] 同上书,第475页。
[40] 同上书,第483页。
[4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22页。
[4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43] 同上书,第41页。
[44] 同上书,第86页。
[45]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7页。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47] 同上书,第235页。
[48] 同上书,第233页。
[4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50] 同上。
[5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7页。
[5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81页。
[53] 同上书,第182页。
[54] 同上。
[55] 同上书,第183页。
[5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57] 同上。
[5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77—178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1页。
[60] 同上书,第252页。
[6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1页。
[6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35页。
[63]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中对东方农业的分析是利用了恩格斯在1853年6月6日致马克思的一封信中的思想。在信中,恩格斯说:“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恩格斯认为,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使得东方国家没有建立土地私有制。“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因此,政府的三个部门中,公共工程部门是很重要的,土壤肥力是靠人工达到的,灌溉系统一遭到破坏,土壤肥力就立即消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0—263页)
[6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65] 同上。
[6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5页。
[67] 同上书,第146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8页。
[6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70] 同上。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2页。
[7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73] 同上书,第181页。
[74] 同上。
[75] 同上书,第230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0页。
[77] 同上书,第19页。
[78] 同上。
[79] 同上。
[8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0页。
[8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页。
[8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页。
[83] 同上书,第105页。
[84] 同上书,第106页。
[85] 同上书,第108页。
[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