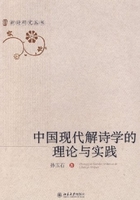
第6章 解诗的必要与解诗学的确立
缩短现代诗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审美距离,是新诗批评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思考。历史与现实都需要这一诗歌美学和方法论的思考与实践。几年前,我在《朱自清与中国现代解诗学》一文中,根据朱自清先生在三四十年代所做的工作,进行整理与归纳,集中阐发了这一思想。
对于这一思考,有人不大赞同。他们提出:“新诗还要解么?诗写得需要别人来解的程度,那还是诗么?”他们是象征派、现代派诗,以及“朦胧诗”、“后朦胧诗”的反对者。观念不同,讨论问题也就无法找到相同的思路。问题似乎不需要回答。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疑惑,不只是这些“道不同,不相谋”者。另外一些喜欢现代诗的人认为,诗,是一个美的整体,它本身不能解释,也不需要解释;一经解释,就破坏了它的完美性。因此,在继续讨论我对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思考之前,有必要重申一下现代解诗学这一理论思考的前提。既然是对于前人思考的整理和归纳,这里还是多引用当时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观点和资料。目的是要证明:这种观念是历史的“重建”,不是新的“发明”。
在中国,还在象征派、现代派诗产生之前,对于一些译介的西方象征派、现代派以及其他流派的诗,对于一些有独特历史和人文背景的诗作,就有人做过非常认真的解诗工作。
20年代初,已经有人在介绍西方象征派诗人的时候,注意到对他们作品内涵的深入把握。如在介绍爱尔兰大诗人叶芝(W。B。Yeats)时,创造社的诗人滕固,不仅肯定了叶芝作品中带着丰富的内涵与“神秘的象征色彩”,“他的象征,也是将不可见的本质,启示绝对的与美的世界;情绪的恍惚,已达极点!”还具体评论了叶芝的诗剧《心愿之乡》,“打破死的恐怖,开自由解脱之门,引人到超越的灵世界;弃去干燥无味的现实,梦见久远的乐境,从不朽的灵魂,涌出真我的呼声;从内面的欢乐,涌出生命的韵律;是精神苦斗的呻吟,与战胜的赞美歌”。文学研究会的诗人王统照,称叶芝是“世界的文坛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处处带有丰富的象征色彩”。王统照详细地叙述了长诗《奥厢的漂泊》的主人公经历过“舞之岛”、“胜利之岛”,到“善忘之岛”的种种漂泊之后,又分析说:“夏芝这篇长诗,确实是藉虚无的意象,表明爱尔兰的基督教和异教徒的冲突。而且用这三个岛子,来象征一个人生的历程。”这是“完全用诗的意境,写出来的夏芝哲学”。这首长诗“在奇幻的思想,与美丽的字里行间,都有他的最大的希望,祈求生命的归依,精神的活动在内”。王统照在翻译另外一位爱尔兰著名作家与诗人娜拉候普儿(1871-1906)的一首诗《黑暗的人》之后,解说了这首很难懂的作品:“我以为这首诗,纯粹是一首象征的作品。所谓世界之玫瑰,是借以象征什么,可难下决定,总是代表人们的最高的精神。末一章所谓:‘仍然立在他们的红灰上’,确系照原诗直译,‘红灰’是种譬喻,或者是作为痛苦的表象,也未可知。”这些点化性的评析里,已经依据象征派诗人的特点,蕴涵着适应解诗的要求而产生的批评思想的萌芽。
20年代末期,闻一多、徐志摩在译介白朗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时,对于这些并不属于象征派的诗,就进行了一首一首的详细读析,为我们作了解诗的典范。
1928年,《新月》杂志的创刊号就曾经以《白朗宁夫人的情诗》为题,同时发表了闻一多先生漂亮的译诗和徐志摩先生更为漂亮潇洒的解释性的散文。
徐志摩在他的文章里,不仅介绍了白朗宁夫人由一个活泼的女孩儿变成终生残废的不幸遭遇,她同白朗宁结识并开始通信的过程,她的甜蜜幸福的爱情生活,这些情诗写作以及如何公布于世的有趣的经过,还对这些十四行诗作了总体的评价,阐述了它们在英国十四行体诗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珍视同时也引起我的兴趣的是,他在这篇被他自己叫做是在“一多已经锻炼了的译作的后面加上的这一篇多少不免蛇足的散文”中,用流利的北京腔和潇洒飘逸的笔调,对前10首诗一一作了解说。每一段文字,都是一篇很好的解诗的实践。
就以白朗宁夫人情诗的第一首为例。闻一多翻译的原诗是这样的:
我想起昔年那位希腊的诗人,
唱着流年的歌儿——可爱的流年,
渴望中的流年,一个个的宛然
都手执着颁送给世人的礼品:
我沉吟着诗人的古调,我不禁
泪眼发花了,于是我渐渐看见
那温柔凄切的流年,酸苦的流年,
我自己的流年,轮流掷着暗影,
掠过我的身边。马上我就哭起来,
我明知道有一个神秘的模样
在背后揪住我的头发往后掇,
正在挣扎的当儿,我听见好像
一个厉声:“谁掇着你,你猜!”
“死”,我说。“不是死,是爱”,他讲。
就其中的典故、个人的生活背景、情感的矛盾、传达的委曲来看,这诗不加以解释,就不是很容易读懂的。这就需要解诗的工作了。徐志摩在解释这首诗的文字中写道:
我们已经知道在白朗宁远不曾发见她的时候,白夫人是怎样一个在绝望中沉沦着的病人。她是一个残废,年纪将近四十,在病房中不见天日。白夫人自分与幸福的人生是永远断绝缘分了的。但她不是寻常女子,她的天赋是丰厚的,她的感情是热烈的。像她这样人偏叫命运给“活埋”在病废中,够多么惨!白朗宁对她的知遇之感从初起就不是平常的,但在白夫人,这不仅使她惊奇,并且使她痛苦。这个心理是自然的,就比是一个瞎眼的忽然开眼,阳光的刺激是十分难受的。
在这第一首诗里她说自己万不料想的叫“爱”给找到时的情形。她说的那位希腊诗人是梯奥克立德斯(Theocritus),他是古希腊文化最迟开的一朵鲜花。他是雪腊古市人,但他的生活多半是西西利岛上过的。他是一个真纯乐观的诗人。在他的诗里永远映照着和暖的阳光,回响着健康的笑声。所以白夫人在这诗里说她最初想起那位乐观诗人,在他光阴不是一个警告,因为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发见轻松的快活的人生。春风是永远骀荡的,果子永远在秋阳中结实,少也好,老也好,人生何处不是快乐。但她一转念想着了她自己。既然按那位诗人说光阴是有恩有惠的,她自己的年头又是怎样过的呢。她先想起她的幼年,那时她是多活泼的一个孩子,那些年头在回忆中还是甜的,但自从她因骑马摔成病废以来她的时光不再是可爱,她的一个爱弟又叫无情的水波给吞了去,在这打击下她的日子益发显得黯惨,到现在在想象中她只见她自己的生命道上重重盖着那些怆心的年分的黑影,她不由的悲不自制了。但正在这悲伤的时候她忽然感觉到在她的身后晃动着一个神秘的形象,它过来一把拧住了她的头发直往后拉。在挣扎中她听到一个有权威的声音——“你猜猜,这是谁揪住你?”“是死吧。”她说,因为她只能想到死。但是那“银钟似”的声音的答话更使她奇特了,那声音说——“不是死,是爱。”
徐志摩的解释文字,简直就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他在对这首诗的解说中,分析了白朗宁夫人复杂的情感产生的心理背景,解释了诗中所使用的古希腊文学中的典故,介绍了她的爱弟悲惨死去的事情,而且贴切地把握了她的婉转曲折充满矛盾的爱的情感。白朗宁夫人这组十四行情诗,还算是比较好懂的浪漫主义的作品,要读者真正了解它们,尚需要做这样的解诗工作,那么,对于那些更加难懂而又有较高审美价值的象征派、现代派诗,为了能够让更多人接受,进行一种解诗学的审美批评,更是现代诗学批评发展的历史必然。
30年代,中国的象征派、现代派诗勃兴之后,逐渐消解了“诗不能解”的观念,是诗学批评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保持诗歌本体的艺术完整与缩短诗歌同读者之间审美距离的同一性,成为许多诗人的共识。现代解诗学理论的出现,就是中国诗学批评现代化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
关于解诗的必要性和诗的可解性,我在此前已经有所论述。这里仅就一个现代派诗人自己的理论表白,对于上述问题再作一点补充。从诗的艺术完整性的角度来看,卞之琳先生反对过细的解诗。他说过,一首被一些人称为所谓的“看不懂的诗”,有时在字句上并没有什么叫人看不懂的地方,那么,让“读者去感受体会就行了”,因为这诗里面“全是具体的境界”,并没有一个死板的谜底在里边。诗的目的并不是要人猜,“要不然只有越看越玄。纪德在《纳蕤思解说》的开端结尾都说‘一点神话本来就够了’。我前几天还写过一句:解释一首诗往往就等于解剖一个活人”。我的理解,卞之琳先生在这里只是讲,解释诗的效果,如果弄得不好,可能会损坏诗美的完整性。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解诗本身,对于诗与读者产生了审美距离之后如何沟通的问题,也没有作出回答。与此同时,卞之琳先生对于解诗工作的这种两难的态度,在另一篇文章中,说得更为清楚。在读了李健吾先生关于他的《圆宝盒》一诗的解释之后,他出来说:自己写这首诗,“不过是直觉的展出具体而流动的美感,不应解释得这样‘死’。我以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近于散文了。但即使不确切,这样的解释,未尝无助于使读众知道怎样去理解这一种所谓‘难懂’的,甚至于‘不通’的诗”。他是担心,对于一首诗的过分“死”的解释,会破坏那种“具体而流动的美感”。同时,他对那些简单地批评象征派、现代派诗为“难懂”和“不通”的诗的观点,婉转地表示了不满。为了消除作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这种隔阂,他还是肯定了李健吾先生解诗的努力,认为这种解释,即使不完全确切,仍然非常有助于“读众”对现代派诗的“理解”。在这里清楚地蕴涵了一个观点:文本解释的诗学批评,在如何帮助读者理解“难懂”的象征派、现代派诗,沟通作者、作品与读者这一方面,是十分有意义而又不可或缺的环节。
诗歌创作中一种客观现象的大量产生,必然促使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独特的诗学批评形态的出现。朱自清先生所首先倡导并努力实践的中国现代解诗学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批评理论。它至今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的出现,使对诗学批评中的宏观现象的审视与微观文本的剖析相互结合,完成了中国完整形态的诗学批评理论的建立。
对象征派、现代派诗抱有理论、审美和心理偏见的人,对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的历史并无了解。他们当然就会对“重建”这一诗学批评形态的思考表示自己的怀疑和否定。可以对一种理论思考表示漠视,但是不能对新诗批评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和开放性表示漠视。这种漠视,已经窒息和终结了多少人为调整现代诗的创造和诗的接受之间关系所做出的努力。